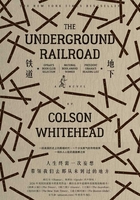
第6章 佐治亚(4)
玛丽在牛奶房上工,跟玛格丽特和丽达一起。在卖到詹姆斯·兰德尔手里之前,她们两个的身上缠绕了太多痛苦的经历,怎么也不能跟种植园的节奏合拍。玛格丽特总在不该出声的时候发出可怕的声音,动物的声音,最悲惨的哭号,最下流的毒誓。主人前来视察时,她用手捂住嘴巴,唯恐唤醒自己对苦难的记忆。丽达不注重个人卫生,不管劝告还是威胁,她毫不动摇。她很臭。
露西和泰坦尼娅从不讲话,前者是因为不想讲话,后者是因为从前的主人割掉了她的舌头。她们在伙房上工,听艾丽斯的使唤,她喜欢这样的助手:不爱整天唠叨,听她讲就行了。
那年春天,又有两个女人了结了自己的性命,比往年多,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到了冬天,没有谁的名字还会给人记住,她们留下的印记着实太浅。剩下的就是奈格和科拉。她们侍弄棉花,从播种到采收,所有的环节一个不落。
这一天的劳动结束,科拉踉跄而行,奈格赶紧上前,把她扶住。她领科拉回伶仃屋去了。工头怒视着她们慢慢走出棉田,但没有吭声。科拉明显的疯态让她免遭随意的责骂。她们从西泽身边走过,他正跟一群年轻的工人在工棚边消磨时间,拿小刀刻着木头。科拉移开目光,在他面前板起脸,自从西泽提出建议,她一直都是这副样子。
乔基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科拉还没好利索。脸上遭到的重击一度让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还给一侧的太阳穴造成了明显的创伤。肿块已经消失,但是银狼吻过的地方,现在留下了一个让人心悸的X形疤痕。很多天还在渗漏。这是宴会之夜给她留下的印记。更为糟糕的是第二天早晨康奈利对她的鞭打,就在笞刑树无情的大树枝下。
康奈利是老兰德尔的第一批雇工。詹姆斯把此人留在了管理岗位上。科拉小的时候,监工的头发还是浅浅的爱尔兰红,因为戴草帽的缘故而卷曲着,宛如红雀的翅膀。在那些日子,他到处巡视的时候,总是打一把黑雨伞,但最终放弃,现在白色的罩衫直接贴着他晒黑的皮肉。他头发白了,肚子溢出了腰带,但除了这些,他还是同一个男人,还是那个用鞭子抽过她外婆也抽过她母亲的人,他迈着歪斜的脚步慢慢走近村庄的样子,让她想起一头老迈的公牛。如果他自己不想快走,就没什么让他走得快的。他只在拿起九尾鞭时才展现一下速度。然后,他会演示一番儿童碰到新游戏时的那种活力和怎么也按捺不住的劲头。
监工对兰德尔兄弟突然视察期间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快。首先,这搅了康奈利的好事,他当时正拿目前上手的娘儿们格洛丽亚取乐呢。他对送信的破口大骂,然后才从床上起身。其次就是迈克尔那档子事。康奈利没向詹姆斯汇报迈克尔毙命一事,因为他的老板对工人数目上的寻常波动从不操心,可是特伦斯的好奇让这件事成了一个问题。
接着就是切斯特笨手笨脚惹出的麻烦,还有科拉令人费解的行为。第二天日出时,康奈利给他们剥了一层皮。他先从切斯特下手,遵循的是犯事以后的规矩:蘸着辣椒水,用力搓他们血肉模糊的脊背。这是切斯特第一次正式挨鞭子,也是科拉半年来的第一次。接下来的两个早晨,康奈利继续鞭打。据大屋的奴隶说,切斯特和科拉倒没什么大不了的,更让詹姆斯老爷心烦的是弟弟染指他的家奴,而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这样,哥哥生弟弟的气,后果却要由家奴承担。切斯特再没跟科拉说过一个字。
奈格扶科拉走回伶仃屋。她们进了门,一消失在村民的视线之外,科拉便昏倒了。“我去给你弄点儿晚饭。”奈格说。
像科拉一样,奈格也是因为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才被重新安置到伶仃屋的。她曾有好些年受宠于康奈利,大部分夜晚在他的床上度过。甚至在监工赏赐些微的宠爱之前,凭着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和波涛滚滚的屁股,奈格就是个孤芳自赏的黑鬼姑娘了。她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对只有她一个人逃脱的虐待津津乐道,喜不自胜。她母亲频繁与不同的白种男人结交,并在水性扬花方面对她言传身教。她横下一条心,献身于母亲寄予厚望的事业,甚至在他换出他们的儿女时,她仍然死心塌地。在大兰德尔种植园,南北两部分一直都在交换奴隶,借着没有章法的游戏,把垮掉的黑鬼、懒散的工人和二流子推送给对方。奈格的孩子成了赠品。当康奈利的穆拉托[3]杂种们站在阳光下,头上的卷毛泛出爱尔兰红光,他是断然不能容忍的。
一天早晨,康奈利明确表示,他的床不再需要奈格了。她的敌人们早就等着这个日子。除了她自己,人人都看得出这一天早晚会来。她从地里回来,发现自己的家当已经给人搬到伶仃屋去了,这就等于向全村宣告她失去了地位。她的耻辱给村民带来了任何食物都提供不了的营养。伶仃屋以自己一贯的方式让她变得强悍。这屋子有助于塑造一个人的个性。
奈格与科拉的母亲从来不曾亲近,但这并未阻止她在科拉举目无亲后出手相助。经过寿宴之夜和随后血淋淋的几天,她和玛丽照料起了科拉。用盐水和泥敷剂打理她皮开肉绽的身体,并确保她吃下东西。她们俩捧着她的头,通过她,给她们失去的孩子唱摇篮曲。小可爱也来看望自己的朋友,但这小姑娘无法不受伶仃屋恶名的影响,看到奈格、玛丽和其他人在场,未免心惊肉跳。她没有跑掉,最后慢慢消除了紧张。
科拉躺在地板上呻吟。遭到殴打两个星期之后,她经历了晕眩的反复发作和颅骨上的一记重击。大多数情况下,她能忍住晕眩,下地干活,但有时只能保持直立,直到太阳西落。每隔一个小时,送水的女孩拿来长柄勺,她便把它舔得干干净净,感觉到金属触及牙齿。她现在一无所有了。
玛丽出现了。“又病了。”她说。她拿出事先准备的湿布,放到科拉的额头。她心里仍然存有母性的情感,哪怕她已经失去了五个孩子——三个没学会走路就死了,另外两个长到能提水、能在大屋周围拔草时就被卖掉。玛丽继承了纯种的阿散蒂人血统,她的两个丈夫同样如此。像这样的崽儿用不着过多的推销。科拉无声地动动嘴巴,表示感谢。木屋的四墙压迫着她。阁楼上还有个女人——凭着臭味就知道是丽达——在翻东西,摔摔打打。奈格揉搓着科拉僵硬的双手。“我不知道哪样更糟,”她说,“究竟是你病了,看不见你的人影,还是特伦斯老爷明天过来,你正好起床出门。”
他即将来访的消息耗尽了科拉的力气。詹姆斯·兰德尔已经卧床不起。他之所以病倒,是因为他前往新奥尔良,与一个来自利物浦的商团谈生意,顺便拜访他那不光彩的世外桃源。返程途中,他昏倒在自己的四轮马车上,此后便再未露面。现在从大屋仆役那儿传出窃窃私语,说特伦斯要在哥哥好转之前接管此地。第二天早晨,他将对北半区做一番视察,以使这儿的生产经营与南半区的行事方式和谐一致。
没有人怀疑,这必定是一种嗜血的和谐。
朋友的手滑落了,墙壁也抽身离去。她昏过去了。科拉在夜的深渊里醒来,她的脑袋枕着一条卷起来的亚麻呢毯子。阁楼上的人都睡了。她摩挲着太阳穴上的伤疤,感觉它在渗出东西。她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冲上去保护切斯特。但当她努力回忆那个急切的时刻、那种让她着魔的细微的情感时,却碰了壁。它已经撤回到她内心深处那个幽暗的角落里去了,不可能把它哄骗出来。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她偷偷溜出门外,走到她的菜地,坐到她的槭木上,嗅着空气,侧耳细听。沼泽里传来嘶鸣和溅落之声,那是猎杀,就在弱肉强食的黑暗里发生着。深夜在那儿行走,向北朝着自由州前进。要那样做,必须与你的理智告别。
可她母亲就那样做了。
阿贾里一踏上兰德尔的土地,就再未迈出这里,好像要与她两相映衬,梅布尔也从未离开过种植园,直到逃走的那一天。对自己的意图,她没露出任何迹象,至少在后来的审讯中没人承认自己知道。在一个充满了叛卖天性和告密者的村子里,这实在是个非凡的壮举,为了逃避九尾鞭的撕咬,他们可以将最亲爱的人出卖。
科拉依偎着母亲的肚子沉沉睡去,此后便再未与她相见。老兰德尔发出警报,召集巡逻队。一个小时之内,追击的队伍便踏进了沼泽,纳特·凯彻姆的狗在前面带路。在长长的专业队伍里,凯彻姆是最新的一个,骨子里就有追捕奴隶的本能。猎狗代代繁育,咀嚼和撕咬过很多不听话的手,专门在周围几个县里探察黑鬼的味道。当这些猛犬奋力向前,扯紧皮带,在空中抓挠,一声声狂吠,营区的每个人都恨不得赶快跑回自己的木屋。但这一天的采摘是奴隶们的首要任务,因此他们听命止步,忍受着群狗可怕的喧嚣,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血腥场景。
广告和传单发到几百英里开外。自由黑人追捕逃奴,以补贴家用,他们在林中搜索,到有共犯嫌疑的人那里打探消息。巡逻队和下等白人组成的民防团骚扰乡里,欺凌弱小。附近所有种植园的营区都被翻遍了,根据行事准则而遭到殴打的奴隶不在少数。但猎狗扑空,狗的主子同样一无所获。
兰德尔聘请巫师作法,对家奴施咒,一定要让有非洲骨血的统统不能逃脱,要逃,则必有惨不忍睹的抽风发作。巫婆在秘密地点埋下神器,领了酬劳,坐上骡车,翩然而去。围绕着符咒的真谛,村里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施咒的对象究竟只是那些有心出逃的,还是所有跨出界外的有色人?一个星期过去之后,才又有奴隶进入沼泽,捕猎,搜寻。那是他们打野食的地方。
梅布尔踪影全无。以前没有人能从兰德尔种植园逃脱。逃奴总是被抓回来,叫朋友背叛。他们误断星座,在奴役的迷宫里越陷越深。回来后,他们饱受虐待,之后才获准赴死,留下亲人被迫在加倍的恐惧中目睹他们走向死亡。
一个星期后,恶名昭彰的猎奴者里奇韦造访了种植园。他和同伴骑马而来,五个外表邪恶的男人,由一个模样吓人的印第安探马带路,此人戴着一条干巴耳朵穿成的项链。里奇韦身高两米,方脸盘,长着锤头般的大粗颈子。他时刻保持着平静的举止,内里却透出杀气,像一片雷雨云,看上去远在天边,可是冷不丁地,它就带着响亮的暴力劈头而至。
里奇韦的拜会持续了半个小时。他在一个小本子上做了笔记,听大屋里的仆人说,这是个非常专注的男人,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他回来时已是两年之后,就在老兰德尔死前不久,亲自为失败致歉。那印第安人不见了,但是有个年轻的黑发骑手,戴着类似的战利品项链,披挂在兽皮马甲之外。里奇韦是到附近拜访一位相邻的种植园主的,他带去一个皮口袋,作为捕获所得的证据,里面装有两颗逃奴的人头。跨越州界在佐治亚是死罪;有时主人偏爱杀一儆百,而情愿不要拿回家财。
猎奴者转述了流言,地下铁道有一条新支线,即将在本州南部投入运营,但一听就知道绝没有可能。老兰德尔对此一笑置之。里奇韦则要主人放心,同情者一定会被连根拔除,还要给他们涂柏油,粘羽毛。或随便什么招数,符合本地的风俗。里奇韦再次道歉,起身告辞,很快他那一伙人便冲向县道,执行下一个任务去了。他们的工作没完没了,需要他们赶出藏身之所的逃奴如同河水,源源不断地带给这白人优渥的报偿。
梅布尔为冒险之旅收拾了行囊。大砍刀、火石和火绒。她偷了室友的鞋子,因为人家的鞋比她的结实。几个星期以来,空荡荡的菜园便是她奇迹的证明。不辞而别之前,她从地里挖出了所有的番薯,对一趟需要脚步如飞的旅程而言,这些东西既是累赘,也不明智。地里的土块和一个个的洞穴,对所有从这儿走过的人都是一个提醒。后来在一个早晨,它们得到了平整。科拉跪在地上,重新栽种。这是她继承下来的遗产。
此时在淡薄的月光下,科拉的脑袋一阵抽痛,她对自己小小的菜园做了一番评估。野草,象鼻虫,小动物参差的足印。宴会以后她再未打理过自己的地。该回来拾掇拾掇了。
特伦斯第二天的到访风平浪静,只有一事略起了些波澜。康奈利带他视察兄长的经营状况,因为距离特伦斯上一次像模像样地参观,已经有些年头了。据大家所说,他的举止出人意料地文雅,没有惯常的讥言诮语。他们讨论前一年的产量,查看账目,其中录有去年九月以来的过磅重量。特伦斯对监工蹩脚的书法表达了不悦,但除此之外,两人相谈甚欢。他们没有视察奴隶,也没进村。
他们骑马巡视田地,比较南北两个半区的收获进度。特伦斯和康奈利穿过棉田,所到之处,附近的奴隶无不以疯狂的干劲加倍努力。几个星期以来,工人们一直在劈斩野草,把锄头刨进垄沟。棉株现在已经长到科拉肩膀的高度,弯曲着,摇曳着,叶子疯长,棉桃每天早晨都大上一圈。到下个月,棉铃便将熟裂,吐絮。白人经过时,她乞求棉株快快长高,高到让她藏身其后。他们继续前行,她看到他们的背影。这时特伦斯转过身来了。他点点头,冲她举了举手杖,然后继续向前。
过了两天,詹姆斯死了。他的肾脏,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