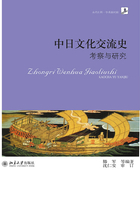
第四节 女王朝贡——魏明帝颁赐亲魏倭王
三国时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国家级往来关系的确定时期。三国之中,魏国的统辖区域最广,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是最强大的国家。而在此时期的日本列岛上,相对稳定的代表性国家——以卑弥呼女王为首的邪马台 国也形成了。由于3世纪时的中日通交仍以朝鲜半岛为主要途径,地处于中国北方的魏国与邪马台国自然成为了三国时期中日交流的主要角色。
国也形成了。由于3世纪时的中日通交仍以朝鲜半岛为主要途径,地处于中国北方的魏国与邪马台国自然成为了三国时期中日交流的主要角色。
在对三国时期的中日交流进行考察时,我们主要依据的史料是《三国志》中的《魏书》。《三国志》是详细记述三国时期,即220年—280年间的史实的,而其编撰者陈寿就是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人。对于当时魏国与邪马台国的交往,陈寿即使没能亲历,恐怕也会耳闻,所以陈寿对邪马台国的记述是详尽的、生动的、可信的。正是由此,《魏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成为了其后的中国正史的引用、转抄的对象 , 《魏书》中对日本的基本观点以及误记也影响了其后千余年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
, 《魏书》中对日本的基本观点以及误记也影响了其后千余年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
陈寿在《魏书》的《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卷》中,在叙述了乌丸、鲜卑、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濊、韩、辰韩、弁韩之后,写到了“倭”。由于书中“倭”字的后面带有一个“人”字,与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写法(文体)不同,所以被史学界习惯地称为《魏志·倭人传》。 陈寿这样处理,笔者认为,恐怕是因为陈寿认为倭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势力集团,还不是一个国家。
陈寿这样处理,笔者认为,恐怕是因为陈寿认为倭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势力集团,还不是一个国家。
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及考古发现,邪马台国是一个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初期的国家,是当时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其国王卑弥呼是一位女王,也是一位宗教领袖,她不和一般人来往,很少有人能见到她,她深居宫室楼观听政、发布命令,唯使一名男子传辞出入,递送饮食。侍奉她的奴婢有千人之多。 在《魏志·倭人传》中的记述如下:
在《魏志·倭人传》中的记述如下: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当时的邪马台国社会还产生有“大人”和“下户”的阶级分化,已有了初步的租赋制,女王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列岛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之间的外交往来。《魏志·倭人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当时的邪马台国,已经从事农耕生产,除了种植水稻之外,还种植一些旱地作物。他们不但已会纺织、缉丝,还能织出倭锦、班布等精细的织物。他们还会酿酒,说明有了多余的粮食。
由于日本列岛气候温暖潮湿,又由于古代中国人的使者只涉足过日本的西南地区,更由于古代缺少科学的丈量工具,记载日本本土情况的第一部中国古代史籍《魏志·倭人传》误把日本列岛的位置记作“在会稽东冶之东 ”。陈寿在描述日本的民俗物产时显出了亲切且轻松的笔调,但他仍指出了日本列岛上的一些独特的情况,如持衰的习俗、搏手跪拜的习俗以及嗜酒、寿考等。其原文的描述如下:
”。陈寿在描述日本的民俗物产时显出了亲切且轻松的笔调,但他仍指出了日本列岛上的一些独特的情况,如持衰的习俗、搏手跪拜的习俗以及嗜酒、寿考等。其原文的描述如下: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簇,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杼枥、投橿、乌号、枫香,其竹筱竿、桃支。有姜、桔、椒、蘘荷,不知以为滋味。有猕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
史载邪马台国管辖有21个国家,有七万余户,基本覆盖了当时日本列岛的发达地区。但在列岛上的南面有一个不属于女王统治的、可以和邪马台女王国抗衡的势力范围,即由男王统治的狗奴国。这恐怕就是邪马台女王国朝贡曹魏、要求册封的直接动因之一。
从西汉到东汉期间,日本不断派人经过朝鲜半岛,到中国“岁时来贡”。由此,日本列岛上生产水平较高地区的部落首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上精华萃集的地区,是在中原的首都。而在这以前,他们所到的、相交往的乐浪和带方,只是中国文明的边地。于是他们就陆续要求直接向首都纳贡奉献了。 当然,初期的日本列岛诸国与中国中央政权的往来还是需要通过中央驻半岛的行政机关的筛选和引见的。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就获得了这样一次机会。但此次机会的获得也与半岛政治的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初期的日本列岛诸国与中国中央政权的往来还是需要通过中央驻半岛的行政机关的筛选和引见的。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就获得了这样一次机会。但此次机会的获得也与半岛政治的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东汉末年,特别是在汉桓帝、汉灵帝、汉献帝(147—220)时期,国势衰落,黄巾起义风席卷全国,趁此机会,周边的小国便开始发生动乱。日本本土也似乎感到了这一点,小国之间加紧吞并,原来的百余国被合并为三十余国。其中的一大势力便是邪马台国。189年,东汉派公孙度赴辽东郡做太守。公孙度见中原大乱,便自己搞起了小山头,他不仅将领地扩至山东,还在乐浪的南边设带方郡,加强其治理。带方郡离日本更近,于是它便取代乐浪,成为了与日本交往的前沿阵地。在《魏志·韩传》里记述“倭与韩同属带方”。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孙子公孙渊共经营此地50年,其间,邪马台国与带方郡有过密切的交往。239年,魏明帝遣司马懿灭了公孙非法政权,收复朝鲜四郡,又令高句丽 臣服,由此,中日之间的往来之路又恢复了。这时,邪马台国便马上派人至魏国朝贺,一方面表示长期以来与非法势力公孙氏来往之过错,一方面,想借助魏国的正统封号来压制住正在与其争夺霸主地位的狗奴男王国。
臣服,由此,中日之间的往来之路又恢复了。这时,邪马台国便马上派人至魏国朝贺,一方面表示长期以来与非法势力公孙氏来往之过错,一方面,想借助魏国的正统封号来压制住正在与其争夺霸主地位的狗奴男王国。

图25 邪马台国的使者朝贡曹魏路线图
239年,邪马台国的使者难升米、牛利在带方太守刘夏的安排之下,在带方郡官吏的陪同向导下,带着男女奴隶10人、班布二匹二丈,步行至洛阳朝贡曹魏。魏明帝曹叡接见了难升米一行,赐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之金印紫绶,赐难升米、牛利银印青绶,之后,其一行才踏上回程。难升米一行人在带方郡官吏的陪同之下再次回到带方郡。240年,带方郡派官吏梯儁等护送魏皇的诏书、印绶、赐品等送难升米一行回日本。
这是中日之间继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后的又一次重要的通交史实。比起上一次来说,此次的日本朝贡是能够统领日本列岛势力的“倭王”的朝贡,并且是在魏国精心策划和安排之下有步骤地进行的一次隆重的外交活动。参与了整个通交过程的带方郡官吏——梯儁等人,通过亲临日本列岛或与难升米等使者的交谈详细地了解了日本列岛的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陈寿在《魏志·倭人传》中对日本的较详尽的描述,中国正史才开始为日本列传,日本正式进入中国的视野。关于邪马台国的首次朝贡的完整过程,《魏志·倭人传》中的原文如下: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縐粟罽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
邪马台国的这一次对曹魏的成功朝贡,不仅确立了邪马台国与大国的正式的册封关系,同时也确立了其在日本列岛的唯一霸主地位,这使得处于统一日本列岛事业之中的邪马台大大受益。可以推想,邪马台人从中国带回那么多的宝物,回国后,在其宫内、在其周围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卑弥呼把金印、铜镜、刀展示给别人看,宣传自己已获得的倭王的称号,这对于日本这一时期的统一政权最终落于卑弥呼之手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而“亲魏倭王”这枚金印不那么幸运,一直没能出土,但在后来的两部印谱里有它的印影,一部叫《宣和集古印史》,一部叫《好古日录》。因这方“亲魏倭王”的金印没有实物可见,所以还无法断定印谱中印文的真伪。

图26 《贡职图》

图27 亲魏倭王印
其后,邪马台女王国又至少于243年、245年、247年与魏国有往来。并且,其往来也越来越有实质性的内容,即魏王朝越来越实质性地承担起邪马台国之宗主国的责任。
243年,邪马台国派大夫伊声耆等来洛阳,这回的正式代表团成员有8人,恐怕带有学习、参观的目的。
245年,魏国送邪马台国黄幢。魏国把黄幢送到带方郡,再由带方郡转赐给等候在那里的邪马台使者难升米。黄幢是一种古代仪式上用的旗子,另一说是车上的帷幔。为什么要送黄幢给邪马台国呢?是否可以这样推测:邪马台女王国与狗奴男王国为争夺在日本列岛上的霸主地位而展开激烈的战斗。女王卑弥呼派人去告诉男王卑弥弓呼,说“本人已是亲魏倭王,有大陆王朝的承认和支持,你们狗奴国就不要再争了”。但男王卑弥弓呼不相信或不理会,还一味地与之争战。于是,邪马台国就需要一种在战场上能一目了然的标志,以此来威慑住对方。邪马台国使者难升米赶赴带方郡说明来意之后,带方郡太守立刻上报洛阳。于是魏朝廷送给了邪马台国一批 黄幢,因为黄幢在战场上十分惹眼,如果真的用于战场上的话,邪马台国的军队将会显得十分威武雄壮。但邪马台国与狗奴国的霸权争夺战并没有因此而告终。
黄幢,因为黄幢在战场上十分惹眼,如果真的用于战场上的话,邪马台国的军队将会显得十分威武雄壮。但邪马台国与狗奴国的霸权争夺战并没有因此而告终。
247年,正值带方郡的新太守王颀 上任之际,邪马台国便派人来求援,看来狗奴国的战斗力强,女王已经吃不消了。魏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属国在日本列岛上的正统地位,这次加大了支援力度,派张政带上诏书、黄幢到日本,为邪马台国做檄文,告谕男王国,请他们投降自制。但等张政赶到日本时,卑弥呼女王已死,开始时立一男王,国中不服,引起动乱,后立卑弥呼的一个女族人为王,名壹与。张政就势宣谕,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于是,壹与在魏国使者的支持下就立住了。有关如上史实的记载原文如下:
上任之际,邪马台国便派人来求援,看来狗奴国的战斗力强,女王已经吃不消了。魏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属国在日本列岛上的正统地位,这次加大了支援力度,派张政带上诏书、黄幢到日本,为邪马台国做檄文,告谕男王国,请他们投降自制。但等张政赶到日本时,卑弥呼女王已死,开始时立一男王,国中不服,引起动乱,后立卑弥呼的一个女族人为王,名壹与。张政就势宣谕,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于是,壹与在魏国使者的支持下就立住了。有关如上史实的记载原文如下:
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根据以上史料的行文语气,可以推测,因张政的日本之行,壹与的地位得到了确立,邪马台国与狗奴国之间的争夺战也落下帷幕。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日往来中,魏国对日本列岛的政治形势、对邪马台国在列岛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邪马台”用日语读为“yamato”,其后的大和朝廷的“大和”二字也读作“yamato”,可见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见魏国对于列岛形势的影响在日本建国初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狗奴国王为什么没派人来魏呢? 可以有以下解释:狗奴国势力太弱,魏国不封;狗奴国没有占领出使用的港口;狗奴国没有像难升米那样的出色外交家;狗奴国力量很强,用不着向中国求助等等。
可以有以下解释:狗奴国势力太弱,魏国不封;狗奴国没有占领出使用的港口;狗奴国没有像难升米那样的出色外交家;狗奴国力量很强,用不着向中国求助等等。
陈寿的《三国志》写于289年,而魏与邪马台的交往只写至247年,为什么双方的交流戛然而止,这要从双方找原因。从日本方面很难查找,因为没有文字史料。如看看中国方面的话,会有一些启发。据记载,247年,曹爽专权,司马懿称病。249年司马懿杀曹爽,掌握朝政。恐怕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邪马台国与魏不便往来。再从日本国内的形势来看,大和国的男权势力越来越强,女王国逐渐消亡,导致中日间的往来逐渐中断。
女王国与魏的通使,不仅从政治上、军事上助长了邪马台国,在经济、生产技术上对邪马台国也是一个促进,同时,也带动了整个西日本社会的进步。比如,在汉字的传播问题上,一般来说,史学界认为汉字导入日本是在应神天皇(270—310)时,百济人阿直岐做了日本皇子菟道稚郎子的汉字老师时开始的。但我们从邪马台女王国与魏的交往过程来看,女王国屡屡向魏上表,魏也多次向女王国下诏,表与诏都是用汉字来表达的。在这种交往中,汉字自然地就传入了日本社会。这比皇子学汉字要早40年左右。皇子学习汉字,恐怕是日本方面正式接受汉字为国家官方书写方式之开端。
在魏国与邪马台国的交往中,文化的交流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人员的交流方面,中方两次派代表团赴日,建中校尉梯儁、塞曹掾史张政等亲临日本列岛,首开中方官员勘察日本的记录。日方有难升米、牛利、伊声耆、掖邪狗、倭载斯、乌越等人到访洛阳或者带方郡,目睹了魏国强大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这些人员的互访,势必对促进中日双方的高层次相互了解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物品的交流方面,中方送给日本的有金印、丝织物、金、刀、镜、采物、真珠、铅丹、黄幢等;日方送给魏国的有奴隶、班布、杂锦、珠等,每一件物品都是一组文化信息的传达。可以指出的是,在239年时,日本上贡的是“班布”,而10年之后248年时,日本贡上的是“异文杂锦”,即中国人不熟悉的、有日本独创花纹的高级丝织物。从中可以看出,邪马台国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长足进步。
关于邪马台的所在位置一直存在“近畿说”和“九州说”两种学术观点。此论争自江户时代至今仍没有定论。
主张“近畿说”的学者有松下见林、伴信友、内藤虎次郎、高桥健自、三宅米吉、梅原末治、大森志郎等。其观点认为:从明代的《混一疆土图》可得知,至明代的中国人都误认为倭是一个以北九州为北端南北展开的列岛,《魏志·倭人传》中所说的“南行”实际上是“东行”。何况在近畿地区已发掘出很多中国三国时期的铜镜,证明在公元3世纪时,近畿地区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更有大森志郎从古日语方面的考察,他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夜摩登”“野麻等”是“yamato邪马台”的注音符号。而如今奈良地区的雅称就是yamato。
主张“九州说”的学者有本居宣长、菅政友、白鸟库吉、桥本增吉、那珂通世、喜田贞吉、榎一雄等。《魏志·倭人传》中的记述虽然在距离上有夸张之嫌,但中国使者不至于把方向搞错,应尊重原始的记述。榎一雄还提出,中国使者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对马海峡登陆日本后来到伊都国,至此的记述是一般采用的线形的行走路线记录。但是使者到了伊都国以后是以伊都国为轴心来记录方向和里数的。即有可能中国使者以伊都国为较稳定的驻地分几次出访了邪马台国、不弥国、奴国、投马国。而今在九州的佐贺发掘出了兴盛于公元1世纪的完整的部落——吉野里。其遗迹包括有坚固的壕沟、国王的行政机关、诸多的物资分类仓库、从北至南的国王居住区、大人居住区、下户居住区。吉野里的发现为邪马台国的“九州说”添加了依据。
实地考察伊都国铜镜遗迹
在《魏志·倭人传》中,有一句话很令人读后发想。
“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意思是说,你在我的万里之外还来朝贡,其归顺之心是不台女王国许多的礼品,其中有铜镜百枚,并嘱咐来访者“汝可将(这些礼品——笔者注)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意思是说,你可将这些礼品展示给国人看,让别人知道,我很同情你,很看重你,所以才给你这么多贵重的礼物。那么这些礼品被运到日本后,是怎样被利用的呢?我们以铜镜为例来探讨一下。

图28 细纹多钮铜镜
其实,传到日本的铜镜并不只这百枚,至今,日本出土了1000多面中国铜镜 ,在公元前2世纪,便有一种多钮细纹镜传到了日本。它的背后有2~3个钮,镜背上画满了细纹,这是中国战国时期东北地方的制品。其后,朝鲜半岛有仿制品,这些仿制品又传至日本。目前在日本出土5面。
,在公元前2世纪,便有一种多钮细纹镜传到了日本。它的背后有2~3个钮,镜背上画满了细纹,这是中国战国时期东北地方的制品。其后,朝鲜半岛有仿制品,这些仿制品又传至日本。目前在日本出土5面。
镜子本是生活用品,在中国出土的镜子正面都是平的,可照出人影,其边缘有一些坡度,整体也可说是凸面镜。但在日本出土的5面半岛制造的多钮细文铜镜的表面却是凹面的。这样的物理结构是照不出人影来的。说明此铜镜在制作当初并不是为实用的。
铜镜在中温、干燥的情况下,可清楚地照出人影,在低温或湿度大的情况下,则表面积上一层似霜的东西,照出的人影不清楚。另外,白天和夜晚的情况下也不一样。所以,日本人便从中感到了灵物的存在。于是,古代日本人就把它当作了祭品。在日本出土的5面多钮细文铜镜中,有2面出自个人墓葬,有3面出自祭祀场,这也说明了这一史实。日本人在祭祀活动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精品镜更应有灵气,于是,便千方百计从中国人那里讨来铜镜,也许中国人也知晓了这一点,魏明帝赐给女王100面铜镜。当240年魏明帝派梯儁正式回访时,又为女王国带去了铜镜。

图29 日本福冈出土西汉铜镜——“清白镜”(直径15.4厘米)
可以说,中国西汉、新、东汉等各时期的铜镜均可在日本找到。比如重圈铭带镜,即有三个同心圆的圈,其间铸有铭文,这是较典型的西汉镜的纹饰。其中的1面还刻有屈原的故事,说屈原“清白而事君,清质以昭明”,日本人叫它“清白镜”或“昭明镜”。这种前汉镜在日本筑紫郡春日町的遗迹里曾一下子出土了30面。其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呢?一定是一位有实力的王。
王莽特别讲究五行,在他执行新政期间,制作了许多方格规矩四神镜。即在镜子的背面有方格图案象征四方,在四方布有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大神兽,在神兽下又配有矩形、T形的花纹。这种新政镜也同时传到了日本,在日本有大量的出土。特别是东汉王朝讨厌王莽留下的东西,恐怕都处理给了日本人吧。

图30 日本佐贺出土王莽时期铜镜——方格规矩镜(直径17.9厘米)

图31 日本九州冲之岛出土中国三国时期铜镜——三角缘神兽镜
至东汉,中国流行内行花文铭带镜,即在同心圆的内部有八条弧形花纹的铜镜。这种东汉镜亦在日本的墓葬中有发现。再要强调的是魏国送给邪马台国的那100面铜镜,也属于内行花文铭带镜,其镜已在日本出土40余面,因其镜边的断面呈三角形,上有“景初三年”的铭文,所以被日本考古界称为“景初三年三角缘铭画文带神兽镜”。
由于中国镜供不应求,到后来就出现了日本制造的镜子,至今已出土了2000多面。其中是否有邪马台国仿制而赐给下属地域王的呢?其可能性是很大的。其特点一是尺寸随意。有的直径46.5厘米那么大,有的只有直径2.5厘米那么小。第二个特点是花纹的变形。由于日本缺少兽类动物,导致日本人缺乏摹写兽类动物的实感,所以在仿制王莽时期的四神镜的时候,产生了图案上的变化,比如,白虎变到最后就被铸成了一个花纹。第三个特点是纹饰有相反的现象。日本的铜镜制造者在仿制中国铜镜时,要看着样品做模子,比如中国铜镜上有一个朝右方向的矩形,工人们照此作出模子,而浇铸出来的就是朝左方向的矩形了。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印证了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积极模仿吸收的轨迹。
1965年1月,在日本福冈县古伊都国旧址的平原村,果农井手信英在挖掘种植柑橘的沟时挖出大量的已破损的铜镜片。后经以原田大六为领衔的考古专家们的研究鉴定,该处为日本弥生时代后期古伊都国的一个王墓。关于伊都国,《魏志·倭人传》中记有:“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平原伊都国王墓为东西6.4米,南北3.5米的一个土坑,中央有一上下可打开的竹筒形木棺。棺内尸体无存 ,从棺中出土的3个大号玻璃质地的勾玉、500余个玻璃质地的串珠、2个耳珰来推测,墓主人是一位女王。最有考古价值的是,在棺外出土了40面铜镜,其中的5面为同范的直径46.5厘米的大铜镜。此墓的所有出土铜镜均为日本仿制铜镜,其5面大铜镜的仿制摹本是中国东汉流行的内行花纹铜镜。
,从棺中出土的3个大号玻璃质地的勾玉、500余个玻璃质地的串珠、2个耳珰来推测,墓主人是一位女王。最有考古价值的是,在棺外出土了40面铜镜,其中的5面为同范的直径46.5厘米的大铜镜。此墓的所有出土铜镜均为日本仿制铜镜,其5面大铜镜的仿制摹本是中国东汉流行的内行花纹铜镜。

图32 福冈平原古迹出土日本制内行花纹镜(直径46.5厘米)
中国古代的铜镜直径一般不超过30厘米,由于日本铜镜的超大化,日本铜镜在仿制中发生了一些改变。如伊都国王墓出土的5面大铜镜的钮周围的花纹由4叶文变为了8叶文,重圆部分上的雷云纹被省略,镜体也相对薄了许多。更值得关注的是,40面铜镜在埋葬前已被完全打碎。这一处理陪葬品的习俗发生在弥生时代的后期的九州地区,并延伸至古坟时代前期的九州和近畿地区。关于把铜镜打碎后再埋葬的原因尚在研究之中,目前的解释为:因铜镜严重短缺,将其打碎后埋葬可增加铜镜的数量感。关于伊都国王墓铜镜的超大尺寸问题,河上邦彦根据《日本书纪·景行天皇四十年是岁条》“将大镜架于船上,使反射光芒照射至陆上敌方,令其知我大王的威力”之句分析推测,大尺寸铜镜是象征王权的祭器,其设计理念是在表现太阳信仰。

图33 伊都国历史博物馆的王墓模型展示
现在,出土了大铜镜的伊都国王墓被修整为“平原历史公园”;其大铜镜等出土文物被收藏于“伊都国历史博物馆”,供人们参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