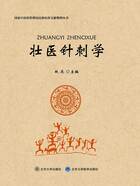
第三节 壮医针刺的发展
随着壮医针刺疗法经验的积累和发展,针刺由民间零散使用走向专人操作,这对促进壮医针刺疗法水平的提高和治疗范围的扩大有着重要的意义。宋代已有壮医(俚医)的记载。如苏颂的《本草图经》“甘蔗根”条有,“今出二广、闽中”“俚医以治时疾”的记载,说明历史上壮医确实是存在的。西周末年,广西武鸣一带的骆越人已经用青铜针陪葬,说明该针为墓主生前常用之物。据发掘情况来看,广西武鸣马头乡墓葬群有三百余座,唯该墓发现此针,且随葬形式与其他墓葬相比,颇为奇特,除两枚精致的青铜针外,只有少量的破陶片。据此推测,墓主生前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部族针刺医。广西贵港银针的墓主是当地的骆越人首领,银针可能是他生前的治病用具。作为南越王国的诸侯,治病必然不用自己动手,既然有专用针具,估计也会有专门的施针人。西汉早期保健医生的出现,旁证了骆越针刺医生很可能在西周末年就已出现。
一、社会进步促进壮医针刺疗法的发展
西汉贵港银针与西周武鸣青铜针相较,针具的形状有了较大的改进。贵港银针针柄很长,且呈绞索状。这种针具便于扩大触及范围,以便在人体隐深部位如咽喉等部浅刺,绞索状针柄便于捻转,控制放血量。从针具的用途推测,在西汉初期,壮医浅刺治疗不仅浅刺体表皮肤,而且摸索出一些隐深部位针刺经验。宋元以后,特别是改土归流之后,经过汉族文人的整理,壮族民间一些疗效独特的治疗经验开始载入史册,逐渐为人们重视。如隐深部位的浅刺急救治瘴法就是其中一例。如宋代广西地方志《桂海虞衡志》记载了“挑草子”疗法的详细情况,曰:“草子,即寒热时疫。南中吏卒小民不问源病,但头痛体不佳便谓之草子。不服药,使人以小锥刺唇及舌尖,出血,谓之挑草子。”《岭外代答》《岭南卫生方》都详记了挑草子治瘴的急救经验。如今,壮医仍用此法进行急救。西汉银针及宋代史载均反映了壮医浅刺疗法隐深部位针刺法的发展成熟过程。
据葛洪《肘后备急方》载,至少在晋代,壮族先民就将针刺疗法用于治疗岭南一些特殊的地方病种。沙虱虫形体细小,针挑需要精细的针具及高超的技术。根据广西出土的刺针分析,金属微针的使用,是可以达到这种针挑要求的。这一记载反映了古越人治疗范围的扩大及地方特色的增强,至今,广西地区的针刺法与中医的调刺疗法相比,治疗病种的广泛程度是一致的。壮医针刺疗法,基本上发挥了中医调刺疗法的作用。目前,针刺疗法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疗手段,仍在广西民间广为采用,尤其是壮族聚居的村寨,一般都有善于针刺疗法的民间壮医。此外,一般群众,特别是妇女更是精于针刺技法,平时出门多随身携带针具,甚至姑娘婚嫁,亦以针具陪嫁,以备不时之需。
壮医针刺治病,选用针具不论是植物刺、动物刺还是缝衣针,均具有“其锋微细”的特点,很少使用针头粗大的三棱针,即使是用瓷针浅刺,也多轻割浅划,避免口大出血多。壮医认为一些针能起到特定的药疗作用,如瓷片能祛风、穿破石刺能清热、柚子树刺能除秽等。
二、社会历史促进壮医针刺疗法的发展
历史上,壮医浅刺疗法曾有过灿烂的一页,但由于地域的局限性,其理论与吸收各族医药之长的中医相比,尚较落后。这一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不平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一)文身习俗促进针刺实践发展
古越人有文身习俗,文身是一种原始宗教崇拜或其他心理追求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国策·赵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袵,瓯越之民也。”《汉书·地理志》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皆粤也。其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苍梧、郁林、合浦皆在广西境内,古为苍梧越、西瓯、骆越人的领地,可见文身习俗在壮族先民中确实存在。一些民族学家认为:断发文身是古越人的唯一特征。古越人这一异于其他民族的奇特现象,是与其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如今,壮族人仍有在手腕上文刻图案的遗俗。文身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晚于医药,但文身是一项全民性的信仰活动,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蒙昧时代,它会激励整个民族去追求、去探索、去实践。整个民族的针刺实践,其经验的总结是少数医家的针刺活动不可比拟的。因此,文身习俗在客观上促进了针刺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这是壮医针刺法在壮族地区迅速发展,广泛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古越人政权促进针刺疗法发展
古越人政权对浅刺疗法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从广西微针的出土得到旁证。
西周末年广西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根据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至战国墓群发掘出的兵器情况分析,当时已经有部族之间的战争。部族生存的需要使越族政权必须重视医疗活动。为了种族的繁衍,古越人各部落必须使用一切医疗手段。由于秦统一岭南之前,广西属荒芜之地,从中原进入广西的人数是很少的,中原地区的医药更是无法传入广西古越人各部落。从当时广西社会生产力发展情况来看,针刺疗法是主要的治病手段,故倍受古越人政权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制作了适于针刺要求的青铜针。金属针具的出现,是广西地区针刺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促进了针刺疗法的专人化,以及掌握针刺经验的部族医生的产生。
从秦瓯战争中广西西瓯人对秦兵的顽强抗击情况看,秦统一岭南之前,古越人的医疗经验已达到一定水平。《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29年(公元前218年),秦派遣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五路用兵岭南,向广西兴安县越城岭进逼的一路秦军,遭到广西西瓯人的激烈抵抗,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西瓯部落如此强大的作战能力,若无一定的保健治疗手段是难以实现的。
(三)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保存了壮医针刺特色
近两千年来,中央封建王朝对广西先实行的羁縻政策后实行的土司制度,对广西壮族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亦使得针刺疗法得以保留,并发展成为今日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疗法。羁縻政策起于汉代,至唐宋一直沿用,宋以后羁縻制发展成土司制。这一政治制度在广西壮族地区延续了一千多年。羁縻政策的采用,保存了瓯越人原有的社会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族文化在瓯越族地区的传播。而在土司制度下,土司世袭,其权力之大犹如土皇帝,正如恩城州治(今大新县)的赵世绪摩崖刻文和《白山土司志·诏令》所述:“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尺寸土地,悉属官基”“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人民没有人身自由,更无识字受教育的机会。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普通人无法阅读中医书籍,且各土司之间各自为政,互相很少来往,汉人更难进来,故汉族医疗技术难以传入壮族地区。汉族治疗方法的传播受到限制,迫使壮族地区必须重视原有医术,并作为主要手段与疾病做斗争。针刺疗法这一具有悠久传统的治疗方法,作为主要的治病手段,一直在发挥作用。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宋代以后的地方志多有记载,此处不再赘述。在羁縻政策影响下,针刺疗法在壮族地区发展有以下特点。
由于针刺疗法简便价廉,适合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长期以来深受壮族地区人民喜爱,并成为他们的主要治病方法。大量实践经验使得针刺疗法自成一体,治病范围愈来愈广。
羁縻制度下,各土司之间来往较少,人民被繁重的劳役地租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各州、县之间来往少,加之千百年来针刺治疗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授,故各地区之间针刺疗法略有不同,各具特色。
自南越王国覆灭之后,广西壮族地区瓯越人再没有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失去了制作统一针具的条件。在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奴隶及农民生活贫困,更无法获得价值昂贵的金属针具,且在壮族地区针刺疗法很常用,故只能沿袭古老的以他物代针的方法。久而久之,广西壮族先民对这些代用品的药疗作用有所认识,逐渐从民族心理上予以接受。故时至今日,瓷针、动植物针仍是壮医师喜用的针具。
壮医针刺疗法产生于广西地区,是在古代广西地区的西瓯、骆越等民族的针刺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广西各地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磨制的精巧砭石、骨针是壮医针刺疗法首先产生于广西壮族地区的最好说明。这些砭石、骨针是随着针刺经验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没有时代更早(旧石器)的针刺实践,亦就没有新石器时代砭石、骨针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