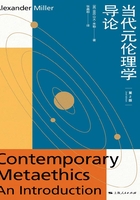
2.3 对经典开放问题论证的三个反驳
本节我将概述对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的三个反驳。
|反驳1| 弗兰克纳的反驳
弗兰克纳(Frankena)写道:
倘若可以指责他人犯了自然主义谬误的话,这种指责也只能作为从讨论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作为决定如何讨论的手段。(1938,465)
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弗兰克纳的反驳,即摩尔的论证相对于分析自然主义者乞题。
首先,只有当“步骤(4)中有一个开放问题”这一信念有充分的根据,我们才能诉诸这一信念。但如果分析自然主义是对的,这一信念就没有充分的根据:认真地提问“是N的x是否也是好的”确实会显示概念上的混乱,尽管我们错误地认为不会。所以,只有当我们已经确定分析自然主义是错的,才能诉诸步骤(4)中的开放问题。由于那正是摩尔的论证想要得出的结论,他就无法在不乞题的情况下,使用COQA去反对分析自然主义。
其次,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思路来看待弗兰克纳的批评。诚然,“令人快乐的行为是否是好的”与“我们欲望去欲望的东西是否是好的”都是开放问题。但从这几个例子得出一般结论说,对任何自然属性N,“是N的东西是否是好的”都是开放问题,则是没有根据的,除非我们已经认为分析自然主义是错的。因此和前面一样,摩尔提出的论证是乞题的。
|反驳2| “无趣分析”反驳
开放问题论证假定,概念分析在为真的同时是不可能提供信息(informative)和有趣的(interesting)。考虑任一概念P,设想它可以依据另一个概念P*来分析。如果这种分析是提供信息和有趣的,那么我们必定可以有意义地提问“是P*的东西是否是P”。根据摩尔的观点,依据P*对P的分析是正确的,仅当“是P*的东西是否是P”是封闭问题,换言之,认真地提出这一问题意味着你不理解它。所以,摩尔的论证蕴涵着,依据P*对P的分析是正确的,仅当这种分析完全是不提供信息和无趣的。然而,这种蕴涵关系是错的,分析显然可以是提供信息和有趣的。例如,数学和逻辑领域可以说隐藏着很多先天的和分析的真理,哲学领域也不乏有趣和提供信息的分析(例如,依据我们以特定方式看东西的倾向来对颜色进行倾向论的分析,将知识分析为得到证成的真信念,等等)。 因此,摩尔的论证出了差错。
因此,摩尔的论证出了差错。
针对上述反驳,摩尔也许会这样回应。开放问题论证并无缺陷,因为一个分析既正确又提供信息和有趣,这实际上的确不可能。“分析悖论”(paradox of analysis)表明了这一点。设想我们试图依据概念C*来分析概念C。假定我们理解概念C,那么,我们便知道概念C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便知道C的意义中包含着什么。如果C可以依据C*来分析,那么C*是C的意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已经知道C*是C的意义的一部分。所以,如果C可以依据C*得到正确的分析,这种分析不可能是有趣和提供信息的。因此,前面的反驳最终不是一个好的反驳,因为分析悖论表明的确不存在有趣和提供信息的分析。
然而,“分析悖论”实际上根本不是悖论。要看到这一点,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没有意识到概念的正确分析包含什么的情况下,如何理解概念?如果我们能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就表明不存在“分析悖论”。一种回答方式是区分技艺知识(knowledge how,即拥有一种能力)和事实知识(knowledge that,即命题知识),然后论证理解概念在于拥有技艺知识,而关于正确分析的知识是一种事实知识。这样就不难解释理解概念的同时,何以缺乏关于概念的正确分析的知识:对大多数技艺知识来说,可以在拥有相关能力的同时完全缺乏描述那种能力的命题知识。例如,某人知道如何驾车拐弯,却不知道正确描述驾车拐弯的那些(非常复杂的)命题。再如,某人知道如何合乎语法地说话,却不能以命题的形式陈述这种能力背后那些极其复杂的语法规则。这些反思表明不存在“分析悖论”,所以摩尔未能成功应对“无趣分析”反驳。
|反驳3| “涵义—指称”反驳
弗雷格有一个著名的区分,即从我们直觉上的意义概念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成分: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他使用的例子是长庚星和启明星。我们知道“长庚星”这个名称意指什么,也知道“启明星”这个名称意指什么,而且“长庚星”和“启明星”意指同一事物。那么,“长庚星实际上是启明星”如何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发现?“长庚星是否是启明星”如何能成为一个“开放问题”?弗雷格认为,“长庚星”和“启明星”这两个名称具有相同的指称和不同的涵义。因此实际上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知道“长庚星”的涵义,也知道“启明星”的涵义,但“长庚星”和“启明星”不具有相同的涵义。尽管具有不同涵义,它们仍然可以得到相同的指称,而它们具有相同指称是我们所能发现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可以在不知道一个表达式的指称的情况下理解它的涵义。例如,我理解“最聪明的三年级学生”的涵义,但不知道这个短语指向哪个人:这是有待我去发现的一件事。
在“好”和“N”的例子中,伦理自然主义者或许也能应用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根据自然主义者的观点,我们知道“N”意指什么,也知道“好”意指什么,而“好”和“N”意指相同的东西。那么,“好这一属性实际上是N这一属性”如何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发现?“具有属性N的东西是否确实是好的”如何能成为一个“开放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说,就像“长庚星”和“启明星”,“好”和“N”也具有相同的指称和不同的涵义。于是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知道“好”的涵义,也知道“N”的涵义,但“好”和“N”不具有相同的涵义。尽管具有不同涵义,它们仍然指称相同的属性,而它们指称相同属性是我们所能发现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可以在不知道一个谓词代表何种属性的情况下理解它的涵义。
对COQA的三个反驳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涵义—指称”反驳是有问题的。摩尔的论证针对的是这样一种伦理自然主义:它主张依据“好”和“N”之间概念的或者分析的等价关系,“是好的”这一属性同一于或者可以还原为“是N的”这一属性。当两个表达式具有相同涵义,它们才分析地等价。所以,“涵义—指称”反驳既然承认“好”和“N”不具有相同的涵义,实际上也就向摩尔承认了定义自然主义或者分析自然主义的不可信。简言之,“涵义—指称”反驳面对开放问题论证所维护的那种自然主义,并不是开放问题论证的批评对象。尽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涵义—指称”反驳是失败的,但摩尔也只获得了空洞的胜利,因为这一反驳表明,存在一种显然不受开放问题论证影响的伦理自然主义。相对于定义的或分析的自然主义,我们可以称这种自然主义为“形而上学的”或“综合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是否可信,是否仍会面临某种COQA?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些问题,第8、9章再讨论它们。
而在我看来,摩尔未能很好地回应弗兰克纳的反驳,他对“无趣分析”反驳的回应也是完全失败的。那么,我们能挽救COQA吗?抑或这些反驳表明摩尔的论证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哲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