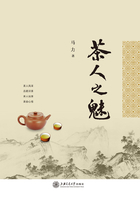
记德高望重恩师何耀曾
我与茶界前辈何耀曾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上海市军天湖农场拥有茶园6000亩,最高年产炒青绿茶达到15000担(约合750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了提高茶叶经济效益,增加外汇收入,急于寻找外销出口之路。那时,上海申江企业总公司总经理薄志明把此事转告了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得到这个信息后,钱樑先生约请李乃昌、何耀曾先生等来到军天湖农场。他们亲临茶园、茶厂考察,从生产经营实际出发为茶叶出口提建议,谋发展,扫除障碍,铺平道路,终于帮助军天湖茶厂解决了绿茶出口的难题。不仅实现了军天湖茶叶由内销转外销的演变,而且使军天湖茶厂成为上海市的出口茶基地之一。自从认识何老后,我常与他通信,以得到他的指教;他也每信必回,诲人不倦。我尊他为恩师,他视我为后生,彼此逐渐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所以,他仙逝之后,我时常怀念他,感恩他。
我们纪念何耀曾先生,因为他把一生完全献给了茶叶事业。何耀曾先生1920年12月9日出生于浙江上虞。1940年至1944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农业系茶叶专科。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教诲,鼓舞他将茶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1949年,他在上海国外贸易总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任业务部副主任,1950年至1954年,就职于中国茶叶公司华东区公司,在储运科先后担任组长、科长。为了新中国的茶业发展,何耀曾心甘情愿,任劳任怨。1956年,茶叶公司在原来拼堆工场、复制工场的基础上成立茶厂,何耀曾担任厂长。由于出口茶都要经过拼堆复制,每年出口量约3万吨,茶厂的工作量非常繁重。厂里有1500多名工人,但是缺乏大型机械,大批量的茶叶要靠人工拼堆装箱。为了完成出口任务,何耀曾和工人们一起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当时按规定厂长家里可安装电话,但何耀曾不要,因为他根本没时间在家里接电话,他日夜奋战在厂里,连谈恋爱都顾不上。能为我国茶叶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1962年,全国红茶会议后,何耀曾又转而投入红茶生产,负责联系江苏芙蓉、四川新胜、湖北恩施等茶场。他经常深入产区,了解生产状况,积极为发展红茶生产身体力行,出谋划策。真正做到了献青春,献终身;舍小家,为大家。
我们纪念何耀曾先生,因为他是上海茶商团队的前辈之一。虽然上海不产茶,但是上海经营茶。特别是在茶的对外贸易方面,早在1685年,上海就有茶叶运销海外的文字记载。鸦片战争前,上海已有茶叶商贸并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抗美援朝时期,美国的封锁禁运影响了我国绿茶对非出口,造成绿茶生产过剩,库存大量积压,茶叶生产面临困境。由于当时红茶供销不足,为了保护茶农生产积极性,寻找茶叶出路,中国茶叶公司在吴觉农先生领导下果断采取应变措施,在重点绿茶产区改产红茶。上海茶商团队是绿改红茶出口的响应者和急先锋。1950年至1980年,上海茶叶出口数约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80%。一个口岸,完成如此巨大体量的出口茶业绩,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有一大批德高望重、兢兢业业的茶人,他们长年默默无闻地为茶叶对外贸易而工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何耀曾先生就是这支茶商团队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爱国、奉献、团结、创新”的茶人精神。
我们纪念何耀曾先生,因为他是上海市茶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81年,全国茶叶会议期间,吴觉农先生与何耀曾谈了上海成立茶叶学会的问题,希望他积极参与,努力把这件事办好。带着吴觉农先生的嘱托,回到上海后,他与钱樑先生等人数次联系市科协和有关部门,向他们说明上海虽然不产茶,但上海在茶叶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力陈上海成立茶叶学会的理由,争取有关单位的支持。经过不断努力,在茶叶公司、外贸局、外贸学院、商业二局等单位的支持下,1983年7月,上海市茶叶学会终于正式成立。何耀曾担任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学会成立之初,条件相当艰苦,何耀曾等老茶人不忘初心,不遗余力,牢记使命,努力工作,克服种种困难,使之站稳脚跟,再上台阶。如今上海市茶叶学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老茶人打下的坚实基础。1988年,何耀曾离休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会建设。何耀曾先生先后担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四、五届理事会顾问,第六届理事会名誉顾问。他虽然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但却时时关心祖国茶叶事业,关心上海茶叶学会的发展,常常过问学会工作,并对学会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何耀曾先生真正实现了“全心全意为茶叶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愿望。
何耀曾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茶人。他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对茶叶事业任劳任怨,竭尽全力;但却默默无闻,甘做无名英雄。他对茶叶学会工作也非常关心支持,出主意,想办法,为办好学会竭尽全力,这是全体学会会员有目共睹的。在茶叶学会组织者的精心安排下,每一次会员交往都是难得的团聚机会,每一次系列活动都留下美好的回忆。茶人相聚,分外热闹,聆听报告,学习交流,以茶会友,以茶交友,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老曾经告诫我,给报刊投稿,有些涉及保密的数字要特别谨慎,不该公开的不能公开,以免泄密。何老曾经送我一份精美的挂历,其中有法国巴黎卢浮宫中珍藏的人体艺术绘画图案。他在1993年12月21日的来信中言:“兹寄上一个挂历,这是法国卢浮宫著名油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我想你不会以封建的残余意识去看它。”在那个年代赠送那样的挂历还是需要有点胆量的。从这些小事中,反映出何老为人的真诚和实在。
还有两件事让我铭记不忘。
第一件和红碎茶生产有关。我记得在军天湖茶厂开通绿茶出口渠道之后,何耀曾先生又提出建议,希望军天湖茶厂发展红碎茶生产,既可增加茶叶花色品种,又可提高鲜叶的附加值和适制性。在何老的建议下,军天湖茶厂决定增加红碎茶出口生产,得到了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于秀澄、许秀梅老师的关心指导。当时茶厂的红茶机械CTC和LTP两种红碎茶加工设备是委托江苏省芙蓉茶厂制造的。芙蓉茶厂的工程师韦祖德先生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接到任务后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把机械设备制造出来并交付使用。该厂还专门派出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实地指导生产,使红碎茶出口加工很快走上了正轨。可见专家技师和兄弟单位的支持有多么重要!
第二件和我加入茶叶学会有关。1983年7月29日上海市茶叶学会成立时,在茶界老前辈的关心下,我很荣幸地成为首批会员,并且参加了在市科学会堂举行的成立大会。我参加学会是费了一些周折的,因为按照学会当时的入会条件,要求是很严的。既要讲学历和职称,又要讲事茶年限和工作业绩等,一个年仅30岁的青年人要想入会,是有一定难度的。结果,我还是被学会破格吸收,成为108位创始会员之一。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是与茶界老前辈钱樑、何耀曾、刘启贵、万紫娟的关心和帮助分不开的。这件小事,让我时常感恩在心。
我常常记得何耀曾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和我是忘年之交,我们的相处很投缘。我在军天湖茶叶总厂担任厂长时,有事就给他写信,以求得他的帮助。他也每每给我回信,给予教诲和指导。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了一首长诗《新茶歌》向上海市茶叶学会《茶报》投稿。何老给我回信:“来信及诗稿收到。诗稿我已转给《茶报》主编徐永成同志,诗稿中你浸透着对茶叶的深情,我十分理解。但诗稿在《茶报》上发表,可能也有一些困难。”“《新茶歌》我希望你琢磨加工,将来可在适当的刊物争取刊出。”虽然当时《新茶歌》没能被《茶报》录用,但是何老是真心实意关心我的。后来,《新茶歌》终于刊登在刘启贵老师主编的上海市茶叶学会论文集中。1993年12月2日,何老给我来信时写道:“一个人的成才除老师外,靠自己实践,靠同志们的帮助,而多读书,学以致用,则一辈子受用无穷,而且书籍这位老师不限于时间,没有任何条件,你可以永远从它那里得到启迪,得到指点,得到帮助。”何老十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告诫我,读书可以增长才识,可以陶冶情操。在增长才识上,学问能提高人的判断和处事能力;在陶冶情操上,学问能使人修身养性和洁身自好。人的天赋有如野生的花草,需要学问的修剪;而学问本身,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使人精确。要把读书和思考结合起来,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这需要我们日积月累地反复阅读并且通过生活实践的不断感悟,只有把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真知灼见。学问不是冷冰冰的知识库,而是要和我们的修养、生命连为一体的。学问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又会反过来丰富我们自身的思想境界。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生命的温度、力度和厚度,帮助我们安身立命。何老还说:“中国文字上,‘学问’两字我觉得最有意思,一个人只要肯学、肯问,就会有很多的学问。”他解释了学与问的关系,告诫我不仅要学而不厌,而且要不耻下问。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只有虚心去问,才能获得真知实学。何老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得出了十分宝贵的科学结论。何老对学问的感悟是多么深刻啊!更可贵的是他能老吾老而及人老,幼吾幼而及人幼,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不是我的科班老师,却是我的终身恩师。
在何耀曾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恩师,缅怀他的高贵品质,寄托我的思念之情。
(原载《上海茶业》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