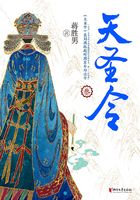
第4章 太后赐封
一月之后,新修建的万安宫落成。
皇太后李氏由西宫嘉庆殿迁居万安宫,皇帝率众嫔妃、皇子,亲王们亦偕同家眷,于万安宫为皇太后设宴相庆。席间母子其乐融融,似乎从未有过芥蒂,好一幅皇家的天伦之乐图景。
百戏过后,李太后多吃了几杯酒,被众人奉承着也十分欢喜,又夸皇帝有孝心,又夸皇后辛苦,这边又笑眯眯地向刘娥招了招手道:“好孩子,你过来,坐到老身的身边来。”
刘娥一怔,坐在李太后身边的楚王世子赵允升倒是早已十分机灵地让出了位置。刘娥见赵恒点头,忙站起来走到前头去,其间,她看到郭熙的身体僵硬了一下才恢复原样。
刘娥走到李太后的身边坐下,李太后拉着她的手,笑得十分慈祥,向着众人道:“这孩子十分难得,又孝顺又懂事,这些日子常来陪老身散心,老身前些日子生了一场病,也亏得她照顾。官家朝上事多,皇后宫务繁忙,也亏得她替你们尽孝心。这么有德行的孩子,若是有人背后胡说八道诽谤于她,老身是不依的。”
郭熙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杜才人差点就要跳起来,被坐在她身边的曹美人及时拧了一把手臂,这才没有失态。
赵恒立刻笑道:“娘娘说得是,刘美人素来待上恭谨,待下宽厚,还多次向朕举荐其他人,朕几次要升她位分,她都谦辞了。朕有时候脾气冲动,也亏得她相劝才没做错事。”
李太后点头:“这是个好孩子。”
众妃嫔眼神乱转:之前宫中刚传了刘美人狐媚惑主封妃被拒的流言,太后这就当众给她立孝名,这是打皇后的脸,还是打宰相的脸?
李太后如今可不管打的是宰相的脸还是皇后的脸,谁的脸一律都没有皇帝的心意重要,她听杨媛说了事情经过以后,就有了打算。
果然赵恒十分欢喜,应道:“娘娘既然夸她好,那赏她些什么呢?”
李太后笑得意味深长:“你的人,要赏也是你赏。”
赵恒就站起来恭敬一礼,道:“既然娘娘说要赏,臣自当遵旨,不如就为她晋升一级位分如何?”
李太后笑了:“既然官家要赏,索性厚道些,这般蝎蝎螫螫地做什么,难道老身的脸面就只值一级?索性升为九嫔吧。”
赵恒就看郭熙:“既是娘娘高兴,皇后,你说呢?”
郭熙站起身,强笑道:“娘娘高兴,自当遵旨……”
赵恒已经兴高采烈地接口:“既然是皇后建议,那就封刘氏为修仪吧!”
刘娥盈盈下拜,郭熙只觉得心头梗塞,却也不得不强颜欢笑。众嫔妃不管心里愿不愿意,也都上前道贺。
等酒宴过后,帝后等人送李太后回去,李太后就道:“官家请留下,咱们母子说几句话。”
赵恒一怔,就令后妃们先回去,问李太后:“娘娘有何吩咐?”
李太后由侍女采玉扶着坐正,目光炯炯,再无醉意:“老身没有什么可吩咐的,只想问你是怎么想的。”
赵恒一怔:“娘娘此言何意?”
李太后叹息:“老身这一生虽没福气生个儿子,但幸而也养了官家,如今官家孝顺,老身也得享晚年。可孙太妃如今膝下无子,连个孙子都没有,这日子就难过了。那个人,你要当真喜欢她,就得为她的将来考虑。”
赵恒有些不安,并不想就这个话题再继续说下去:“娘娘,我自有分寸。”
李太后却道:“今日喜庆,老身就仗着酒意多说几句。老身做过错事,幸而官家不计较。老身也念你的好,所以哪怕得罪人的话,老身也是凭良心说了。就算不提刘氏,只说你。官家,老身服侍先皇这么多年,先皇有八个儿子活到成年,老身自问这个母亲做得不算失职。可你如今膝下只有一子,老身替你日夜忧心哪!”
听她说得情真意切,再细想往昔之事,赵恒也不由得有些感动。
李太后待他,除了在继位之事上私心偏了楚王之外,其余事情,皆是极尽母职了。他曾经为此耿耿于怀过,可心里若撇了这份执念,非亲生的母子,处到这份上,也算难得了。因此心里最终还是迈过了这个坎,待李太后依旧孝敬。
他能够这般对李太后,李太后自然也念他的好,有些话一半是出于私心,一半却也是真心诚意:“官家青春正好,正要趁这时候多生几个孩子。一则,你自己将来有个选择的余地,不必被皇后拿捏在手里。二来挑个喜欢的,抱给刘氏,或可抱子得子,或她自己养熟了,将来也能当个倚仗,我瞧你那个皇后将来未必肯包容刘氏。官家,老身也没几年活头,不怕犯忌讳。有说错的,你也别见怪。”
赵恒长揖为礼:“娘娘句句皆是金玉良言,如今也只有娘娘肯对我说这样的话了,我感激不尽。”
李太后看着皇帝走出去,长叹一声。
采玉低声道:“您这是替杨娘子找出路呢!”
李太后叹息:“为了她,也是为了刘氏。真孝顺的孩子,我哪能不为她们着想呢?”
采玉忧心道:“圣人要知道了,怕是会……”
会什么?会记恨上她这个太后吗?李太后冷笑一声。那若是个得宠得势的皇后也就罢了,可惜,她并不是。
自己待她再好又怎样?若没有自己当日选她为襄王妃,哪来她今日的皇后之位?枉自己当年这般照顾她、关爱她、提携她,结果她竟是个冷血之人,一朝得志,先拿自己这个太后作践。那么就要让她知道,自己这个太后既能执掌中宫许多年,便必不是个无声无息的存在。
李太后迁出嘉庆殿后,赵恒下旨,将正四品美人刘氏晋封为正二品修仪,迁居翠华殿。
这边刘娥被封为修仪,另一边则是另一桩喜事:八月中旬,她的兄长刘美正式迎娶钱惟演的妹妹钱惟玉。
这门婚姻一边是皇家外戚,一边是吴越王孙,又是御赐的婚礼,自然办得隆重无比。婚礼那日,甚至连赵恒都携着刘修仪亲自到府,赐下大量珍宝以示道贺。一时间,刘氏家族颇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势。
说话间又将近岁末,皇后长嫂进宫谒见。
郭熙为人一向简朴,郭氏家族的眷属进宫谒见时,若是有人服饰过于奢华,她必然不悦。因此谁也不敢着华服见皇后,便是宫中嫔妃见郭熙时,也不敢打扮得太过华丽。
郭熙长兄郭崇德承了官职,这次长嫂进宫,郭熙也是很高兴,忙问了家中事务。郭夫人便说起长子郭承寿今年已经十七岁了,也正打算要在来年新春成亲。郭熙听闻十分高兴,忙细细地问了女方家的情况,又叫人备了礼物准备赐下。
郭夫人忙起身谢过,小心奉承着郭熙,说了半日,见郭熙脸色甚好,这才吞吞吐吐地道出来意——却原来郭崇德夫妻见了前几月刘美成亲时的盛况,便想托郭熙向赵恒请旨,比照着这样儿,也同样办一个御赐的盛大婚礼。
郭夫人笑道:“圣人是知道的,爹爹生前立下家规,子弟为官者除俸禄外不取分文。外头瞧着咱们是皇亲国戚,个个伸手,殊不知家里如今也艰难。这门婚事若办得俭省了,文武百官面上不好看,也给圣人丢脸。先头太宗皇帝在时,也曾经给过恭孝太子的岳家恩典,赐予钱财办过婚事,有过旧例。再说,咱们不论拿多少银子来办,到底比不得官家恩典的体面。且如今圣人是中宫皇后,咱们自然也不能教个银匠给比下去了。”
郭熙不听这话犹可,一听之下正刺着痛处,顿时冷笑道:“你在这里说了一大串子的话,我倒听出来了,无非是看着刘美的婚礼眼馋了,也想依样画葫芦罢了!”
郭夫人正想说一声“圣人英明”,还未出声,郭熙已经沉下脸来,骂道:“我的祖父在后汉高祖时就是护圣军使,我的父亲更是大将军,随太祖、太宗皇帝平过后蜀,定过南唐,征过北汉,打过契丹,唐河之战打得辽人闻风丧胆,太宗皇帝赐谥号忠武,追封谯王。我们郭家世代将门,我母亲出身的梁氏亦是书礼世家,我是中宫皇后,天下谁不敬仰!不承想到了你们手中,好的不学,竟要去学那银匠的暴发户作风。你是从那南山的北屯里出来的?见着人家多摆几桌酒,多置几件金器,就哭着喊着要学人家的样儿?没得丢尽我们郭家的脸面!”
一席话骂得郭夫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吓得磕头道:“圣人息怒,原是臣妇无知,臣妇再也不敢了。”
郭熙一番话骂下来,自己亦是气得满脸通红,侍女燕儿忙捧上茶来,郭熙就着她的手喝了一口,这才慢慢地缓下气来,叹道:“你也是世家之妇,怎么这般眼浅!我这骂的也不只是你,我也知道,这断乎不是你一个人的主意。我这几个兄弟,竟是没一个争气的。我在宫里拼死拼活地挨着,你们倒在外头学人家这般小眉小眼的。你们给我争点气罢,纵不能给我长脸,也别给我添堵,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燕儿看着郭熙的脸色,这才上前扶起郭夫人,道:“圣人的话,您可听明白了?”
郭夫人连连点头:“是是是,我明白了。”
燕儿含笑道:“您还是没明白呢!圣人一心教养二皇子,哪里有空去同后宫的那些个无知妃嫔计较!”
郭夫人恍然大悟:“是,臣妇全明白了,臣妇这就回去转达圣人的意思。咱们郭家家风原是简朴重德,倒不在乎外头这些虚的。”
郭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罢了,婚事——终究还是要办的。燕儿,吩咐人从我的脂粉钱里拨些银两给承寿办婚事。”
燕儿忙应了一声,郭夫人不承想还有这份恩典,含泪跪下磕头道:“臣妇代子多谢圣人的恩典。臣妇等一定牢记圣人的教诲,绝不敢再让圣人生气了。”
郭熙看着郭夫人离开,眼泪忽然就落了下来。
燕儿见状惊道:“圣人何以如此?”
郭熙哽咽:“是不是连宫外都觉得我教刘氏占了上风了?官家为了哄她开心就可以陪她到府观礼,而我家,哥哥嫂嫂们再羡慕,我也办不到。我开不了这个口,我在官家那儿也没这个面子。”
燕儿忙道:“圣人不去请才是对的,凭什么那银匠来这样一手,咱们就要跟着,岂不是自降身份?圣人这话放出去,人只会说圣人这样才是中宫皇后的做派呢。”
郭熙苦笑一声,她如今也只能这样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了:“不明白的人,说几句闲话,于我有何益?真正的明白人,还不是一眼看透了。”
燕儿急道:“管他们明不明白,圣人都是当今皇后。圣人有嫡皇子,有圣人在一天,她就算再有心思,官家再宠她,她也就是个无子之嫔。”
郭熙冷笑一声。若是素日,她听了这话,也会心里得意,可此时听来,却是万分难受:难道除了这个皇后名分和一个嫡子外,她就再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吗?她本以为自己已经毁了那个人的晋升之路和名声前途,那么将来,就还可以慢慢剥夺皇帝对那个人的宠爱,甚至一切。
可是没有想到,太后居然会与皇帝联手,打碎她的谋划。她才是中宫皇后,她才是皇子之母,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待她?皇帝偏心也就罢了,她自问待太后一向恭敬,便是那次移宫之事,她也是奉命而行,太后不敢去怪皇帝,却记恨于她,不给她脸面,实在好不讲理。
这一次,那个被她踩下去的人又被太后拉了起来,拉得比原来更高,高到让她感觉到了威胁,甚至在某些地方有越过她的可能。
她绝不允许。
刘府郭府,两边的喜事只相差了几个月,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光。郭氏族人这边婚事固然低调,却是不断地宣扬郭熙自出脂粉钱为娘家人办喜事,不费国库的贤德。恰是对比前几个月刘美婚事的张扬,令得京中官员不由得将两处比较了起来。
“比较?”翠华殿中,刘娥淡淡地道,“比什么?”
雷允恭低下了头,不敢回答。
刘娥笑道:“我知道,必是那一等一的好话儿——什么圣人贤良淑德、不事奢华、抑制外家请求、公私分明,不愧是我大宋皇朝一国之母,郭氏家族不愧为名门望族。相比之下,我刘氏出身低微却恃宠生骄、行事暴发、上不得台面,活脱脱是那南山的北屯里出来的小眉小眼——是也不是?”
雷允恭吓得忙跪倒在地:“娘子这话从何说起?吓煞小的了。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如此毁谤娘子您呢?”他偷眼看着刘娥,小心翼翼地道,“其实京中人人都说,天底下有几个世家能够比得上吴越王府呢?天底下又有几人能够得到官家御赐成婚的殊荣,甚至是官家亲临这种天大的恩典呢?人人都说娘子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连圣人的外家也求不来这等荣耀。满京城的人谁不羡慕娘子您呢,又有谁不羡慕刘将军福泽深厚,能够得到吴越王府郡主的垂青呢?”
刘娥苦笑一声:“羡慕……下层小吏自然是羡慕的,可是那些名门望族还不知道怎么笑话我们、轻视我们呢!”
她只觉得胸口似有东西梗住了,煞是难受。若无刘美婚事的张扬,郭熙也不会故意让郭家人将婚事办得低调。然而刘娥却是不得不张扬,她与刘美前半生颠沛流离,无亲无故,无投无靠,受人轻贱。她是一道诏书被扔到郊外,一乘小轿悄然重回宫门,纵然皇帝待她百般好,她此生仍愿看到有一场正式的盛大的婚礼。便不是她自己,是她的亲人也好。
谁能够想到,当日蜀道上逃难的两个异姓兄妹,到今日一个嫁与当今天子,一个得娶吴越王孙呢?正当她沉浸在刘美婚礼那日的喜悦和欣慰之中时,郭熙却以这种行为嘲笑了她。从上次的封妃之事,到这次的婚礼比对,郭熙从来就没有放过她,一次又一次用自己最擅长的名分大义羞辱她。
雷允恭忽道:“小的明白娘子想的是什么,不过恕小的大胆地说一句,娘子何必在意他们的想法呢?”
刘娥冷笑一声:“你懂什么?哼,我不必在意什么,又必须在意什么?”
雷允恭忙磕头道:“小的不敢,小的只是一个内侍,眼界看法也只是一个内侍的眼界看法罢了。小的只是觉得,刘将军娶了钱家娘子是一桩美事,一桩天大的喜事。能够得到御旨赐婚,婚礼上天子亲临,更是难得的殊荣。官家肯为娘子做这么多事,是因为官家喜爱娘子,为了满足娘子的心愿,让娘子高兴。这事儿娘子面子里子都有了,人人都知道您会高兴,只有一个人会不高兴,那就是……”说到这里,他不由得向门口看了一下,确定不会有人进来才继续,“那就是希望您不高兴的人。这世上除了您,还有谁能得这份殊荣?就算勉强求了来,也是落您后头。这人要是什么都比不上您,那也只有变着法儿弄些事儿出来让您闹心。您说您要为这事儿心里不舒坦,那官家待您的这份好这份心不就白费了?”
刘娥不由得点头:“你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
雷允恭道:“娘子是何等明白的人,前儿封贵妃的事,您自己还劝杨娘子呢,怎么在这件事上就想不开了?”
刘娥一怔:“是啊。”不由得自嘲一笑,心想:可见之前的事,我也不过是说给自己开解罢了,终究是放不开的。一而再,再而三,其实都是堵着这口气呢。
雷允恭又道:“您想,谁都见着您盖过人家了,该生气的是那边。那边不过空口白话地发个牢骚给自己搬个梯子下罢了,您又何必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呢!这种牢骚越多,说明您的分量越重啊!”
刘娥听了这话,心里竟是一松,郁气稍减。正在此时,如芝来报,说刘夫人来了。
宫外这样的言语自然也传到了刘美府中,当时刘美就要让钱惟玉入宫请罪,早早递了请见的呈文,刘娥允了。
这时候钱惟玉匆匆到来,见了礼以后,刘娥见她神情,就令左右退下,只余如芝,这才问:“嫂嫂有何事?”
钱惟玉就道:“前儿夫君听了郭家的传言,深恐娘子受连累,就让我入宫请罪。”
刘娥就道:“嫂嫂不必忧心,我无事。”
钱惟玉松了口气,道:“我也料娘子无事,夫君还忧心娘子会因此着恼。年前圣人的嫂嫂到宫里来求恩典,教圣人骂了出去,如今编出这种话来,要我说,也只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我都明白的事,娘子这样的聪明人,哪里会自己钻了牛角尖?”
刘娥一怔:“嫂嫂也这么想?”
钱惟玉笑道:“不这么想,还有别的想吗?世人都知道,有体面谁不爱,郭家若请得动官家,哪里还用得着编出这种酸话来!”
刘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笑了:“你说得对,是我着相了。”
钱惟玉又道:“我入宫前,兄长也来叫我同娘子说,请娘子放心,这并不是咱们和皇后两边的事,包括当日封贵妃的事,也不是后宫之事。皇后固然有援,娘子也并非无援。”
刘娥一怔:“这是何意?”
钱惟玉就细细将钱惟演的话复述了:“我兄长言道,这是朝中北方官员和南方官员借此闹不和……”
大宋是建立在后周基础上的,立国之功臣多出自北方大族。后一统天下,收南朝降臣入朝,南官一开始就比北官低一头。可是马上得天下,总不能马上治天下,若论经济事务,终是南官更胜一筹。尤其是太宗皇帝在时,大开科举,引天下才子入京为朝廷所用。而这科举,南方才子又胜过北方才子,这就埋下了朝堂上南北之争的隐患。
太宗皇帝临终之时,曾贬寇準入地方,直至官家继位,才召他回来以重用。可是寇準如今就公然排斥南方官员,已招致诸多非议。
钱惟玉说的,刘娥早已有所察觉。先时杨媛不理解她为何在后宫之中一味退让,却未曾想过,皇后、曹美人、杜才人等均出身关洛世家,如今朝堂上南北之争又起,后宫一点茶杯里的风波,闹到宫外去,就成了滔天大浪。
就听得钱惟玉又道:“兄长言,恐怕长此以往,南方才子会对科举失去信心,对朝廷失去信心,若有割据势力再起,岂不为人所用!如今南方赋税已经占了国库大半,南方的户籍人口也占了国之大半,可内阁决事的宰相之中有几个南方人?若内阁长期只有北官而无南官,施政焉能不对国策的走向产生不利的影响?”
刘娥顿时想到,当年王钦若也曾经差点被点为状元,旨意虽然还没下,但大家都知道了,同窗来向他贺喜,他一高兴喝多了,本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本来就有人不希望他一个南方人当状元,就上了一封弹章,说他袒腹失礼。太宗皇帝原本旨意都写好了,却因此临时改了人,王钦若只得进士甲科及第,如今也并未入阁。
想到此处,刘娥就对钱惟玉道:“你们放心,我明白的。”
她并非孤独一人,她的身后是南官,也是南人,更是将来大势的走向和皇帝需要的方向。
这一战,从来就不是她和皇后之战,而是朝堂之争的延续。而最终,南北官员之争,也将决定大宋江山的走向。
晚上,赵恒如常在看着奏疏,刘娥坐在一旁相伴,但她却不再如往日一般,只是相伴而已。
虽然当日在赵恒争储之时,她不免牵涉其中,也有所建议劝谏,但她也知道后宫不可干政,所以在赵恒继位之后,尽量避免干涉。毕竟争储之时,她不过是在赵恒低落时给些鼓励,也会针对诸王以及先帝的性子给些建议。但赵恒当了皇帝,却又不同。他每日在朝堂之上要听无数朝臣的建议,要处理万千国计民生,她一个后宫妇人,什么情况也不明了,只能是在赵恒与她细说以后,谨慎地说上几句罢了。
但如今她心境又有不同,再看赵恒伏案办公,心中也不免怜惜起来:“官家,你也歇歇罢,别累着了自己,反而误了事情。”
赵恒疲惫地打个哈欠:“如此多的奏疏,怎能歇歇?”
这边接了她递过来的灵芝汤喝了,叹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各地的奏疏如雪片一样飞来。南涝北旱,夏州又蠢蠢欲动,还有辽人也在生事。当初父皇让我不要只看国内,还要看看周围,此刻才知父皇的深意啊。”
刘娥安慰赵恒:“饭一口一口吃,事一步一步来,若事事急躁,一登基便要天下太平,就欲速则不达了。”
赵恒失笑:“小娥越来越会劝人了。”又道:“实是事情太多,我放不下啊。”
刘娥就道:“却是什么事情?”
赵恒见她有兴趣,也想着放松一下,就道:“你可知最近朝堂对寇準的非议?”
刘娥心中明了,便道:“南边士子若是知道了,怕是要寒心!”
赵恒道:“说得很是。大宋立国数十年,朝堂官员还公然持地域偏见,难道南人竟不是大宋子民不成?”
刘娥见他恼了,忙岔开只说两边话:“臣子们有私心,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为君者当掌控两边的平衡,不让一方失控才是。”
赵恒不由得点头:“你说得很是。只是我也难哪,顺得哥情失嫂意。哪怕不偏不倚,也被人认为我偏着南人。”
刘娥笑道:“我就想起三郎说的,田元均为三司使,常被各种请托包围,不敢应允,又不敢得罪人,跟你诉苦说自己日日赔笑,笑得面似靴皮。想来这苦楚,君臣应是同理。”
赵恒笑得拍案,倒将郁气一扫而光,道:“三司主管财政,既是他不能应允的,何以还要赔笑?可见是请托之人把国库当成私库般随意了。”说到这里,又恼怒起来,“官职、库银、科场,竟都能被他们北官任意指派,他们眼中哪还有天子!”
刘娥又劝:“可见三郎任人得当。我听你说过,去年的开支就极大,到处都是用钱的时候,若三司的钱管不好,万一北边有什么兵事,可就难了。”
赵恒点头:“所以三司得用之人,不只是要管好国库,更要用活财源。”
他说到这,想起一事,道:“三司盐铁副使丁谓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当年他曾采用以盐换粮的办法,解决夔、万诸州军饷之弊,同时也减轻了边民长途解送皇粮的劳苦。又奏请准许黔南边民之马在市场自由交易,解决边民纠纷。还曾规划经营建筑夔州城寨,以增强边防。这个人是西汉桑弘羊一类的人,于经济上很有办法。”
刘娥笑道:“官家如此说,想来此人有极强的才能。”
赵恒点头:“正是。难得他人缘极好,连寇準这样难弄的人都与他是好友。”
刘娥一怔:“这倒难得。”心中暗忖,桑弘羊虽有才华,却是名声不好。此人既有桑弘羊的才干,还人缘极好,可见不是个普通人。
咸平二年(999)秋,边关忽传急报——辽国萧太后亲自率兵,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帅,南下侵宋。
赵恒未继位时便已经十分关心与辽国的边事,只是登基之初,他当以掌握朝中政务为要。此时他登基已经两年,内外政务诸事皆已渐渐熟悉,本也就打算重新整顿军务,听说辽人犯边,便打算亲自巡幸边关诸重镇。
他向刘娥提起此事时,刘娥一惊:“你何以有此念?”
赵恒道:“太祖皇帝是马上得的天下,父皇、大皇兄都上过战场,唯独我从来没去过北疆,没上过战场。这一次边关告急,我与群臣商议,这才发现,不管是边关的将领还是边关的情况,我都一无所知。今儿军情来报,诸位大臣都在那激烈讨论,我坐在那里,却发现什么话都插不上,无法做出正确的决断。这……不是一个天子应该有的状态。”
刘娥听他说得认真,道:“官家,你还有文武大臣,各司其职,并不一定需要你亲自上战场啊!”
赵恒摇头道:“我不是上战场,我只是想去实地了解情况。为君者,不能只会垂拱而治,朝臣说什么都无法判断。军国大事,事关江山社稷,我心里没底,怎敢妄下断言?我要做真正的天子,就要有自己的判断。”
刘娥渐渐有些明白了,她握住赵恒的手:“好,这才不愧是我的三郎。”既知他并非亲临战场,虽有艰难,想来并无危险。他自幼长于宫中,虽然有怜惜黎民疾苦之心,但毕竟大宋立国未久,北有强敌,又怎能不知军事。
赵恒又道:“其实我也是想趁着自己年轻,还有这份热血和胆气,出去看看。我若只在京城之中,怎能知天下事?这一次,我要北巡。我是天子,要去看看我的国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要在大臣们争论天下事的时候,知道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
刘娥盈盈而拜:“那臣妾就静候陛下佳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