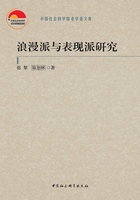
一 时代名称问题
歌德的首次意大利之行(1786—1788),标志着德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古典主义与浪漫派相继出现,此后毕德麦耶派和青年德意志派也接踵而来。与此同时,文坛上还有克莱斯特、让·保尔、荷尔德林等一些不属于任何派别的所谓“无党派”名流。一个人没有名字,不可想象;同样,一个时代如果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时代名称,使众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有个共同的归宿,那也是不堪设想的。但是给这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一个什么名字呢?文学史家们虽然煞费苦心,却始终找不到一个众口可调、皆大欢喜的方案。不可否认,不少方案都是富有建设性,有一定依据和言之成理的。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吧。
一种意见认为,歌德响当当的名字理应成为时代的名称。其主要根据是诗人在当时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尽人皆知,歌德是当时德国精神生活的中心。马克思把他誉为当时最伟大的德国人。恩格斯尊他为自己领域里“真正奥林帕斯山的宙斯”。海涅称他为“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代表”。诺瓦利斯推崇他为“地球上文艺精神的真正总督”。弗·施莱格尔也称赞说,“歌德的文艺是真正的艺术和纯正的美的曙光”。总之,歌德是万众景仰的人物,在文坛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用他的大名作为时代名称应是顺理成章的事。1828年,海涅仿效了伏尔泰的先例,首先提出了以歌德的名字为时代的名称。不过,伏尔泰与海涅的做法显然存在差别:前者把艺术的鼎盛时期列入时代的大统治者的名下;后者则把艺术的黄金时代冠以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名字。按照海涅的理解,歌德时代“从歌德的摇篮岁月开始,在他寿终正寝告终”。它“囊括所有在自治艺术原则下的德国文学,包括‘浪漫派’在内”[1]。近一百年后,1923年,著名文学史家赫尔曼·柯尔夫给他的4卷本断代文学史巨著冠上了《歌德时代的精神》的书名,力图使时代的名称统一起来。但是,不论是海涅的努力或是柯尔夫的努力,在文学史界都没有产生什么反响。为什么以歌德的名字或者以历史人物的名字为时代的名称行不通呢?因为它无法体现文学的时代倾向与特征,从而违背了德国文学史的传统。同时也因为这样做过分突出了歌德的地位和作用。
另一种意见主张以古典文学为时代的名称。在德国,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较多。按照传统的观点,德国古典文学,是指歌德首次意大利之行以来歌德和席勒的创作,特别是他俩合作时期的创作。这种观点植根于19世纪德国文学史家们的著作。戈·格·格维努斯在他的代表作《德意志韵文民族文学史》(1834—1842)的导论里这样写道:“歌德和席勒(把我们)引回到一种自希腊人以来无人曾超越、预料的艺术理想。”[2]这就是说,在这位文学史家看来,歌德和席勒的诗艺超越了文艺复兴时代,超越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艺术,是古希腊艺术理想的再现。
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传统的观点,这种由两位诗人独霸古典文学殿堂的格局,不时遭到非议和挑战。人们指责这种古典文学殿堂根基浅薄。因为它排斥了同时代许多重要作家。同时也因为这里所说的古典文学,时限实在太短,前后不过十年或者十多年。最早起来抨击这种模式的是小说家兼戏剧家卡尔·古茨柯夫。这位“青年德意志派”的代表人物在《仅有歌德和席勒?》(1859)一文里写道:“席勒和歌德表现不了文学创作的整个领域,表明不了只有德国文学需要变化的诸种途径。我们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有诸多不可少的事物,而不论在席勒还是在歌德那儿都找不到相应的表达。”[3]他把克莱斯特和让·保尔抬出来,以打破歌德和席勒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让·保尔在某种意义上比歌德和席勒更为重要。同年,保尔·伯克曼在《历史和现代中的宗教》一书中的《古典文学》一文里把莱辛、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让·保尔和维兰德也列为古典作家。在我国,维兰德一直被打入冷宫。但是评论家维·马尔施认为,根据今天的认识,应对这位作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对于魏玛古典文学来说,维兰德与歌德的篇章,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歌德和席勒的结合,这一结合自一百五十年来已被捧为德意志文化偶像了。”[4]八年后,1867年,威廉·狄尔泰以他的巴塞尔就职讲课,《德国1770—1800年诗的和哲学的运动》,开了更新陈旧的古典文学观念的先河。他力图把从莱辛到浪漫派开始时诗和哲学的发展,描写成为一个“新的生活观和世界观的统一体”。沿着狄尔泰开创的传统,柯尔夫(以他提出的“歌德时代”的概念)和赫尔曼·诺尔(以他提出的“德意志运动”)都力图更新旧有的古典文学概念,拓宽时代的定义。与此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也表示了近似的看法。赫尔穆特·霍尔茨豪尔(《歌德的世纪》导论)把从莱辛到海涅的整个时期,看作“一个统一体”,将它称为“德意志古典文学时代”。在他看来,把一个统一的时代分解为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古典文学、浪漫派、毕德迈尔派和三月革命前时期等的对立的或类似的现象是不恰当的。卢卡契也认为德国古典文学应包括“从莱辛到海涅的进步文学”。但是他把浪漫派视为一股逆流。这个流派自然要被他拒之于古典文学殿堂大门之外了。
可见,更新德国古典文学旧观念的呼声大有愈来愈高之势,但是旧的观念和传统仍有相当的势力,要使新的观念和传统被普遍所接受,谈何容易。
第三种意见主张以浪漫主义作为统一的时代名称。这种主张简直是对德国传统观念的严重挑战。由于种种原因,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魏玛古典文学和以施莱格尔兄弟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在它们本国和国外的境遇是很不一样的。纵观它们在国内外的接受史,谁胜谁负的问题,无法盖棺定论。如果说前者在国内享有某些优势,那么在国外情况往往倒过来了。当今,德国以外的西方学者,主要是英法国家的德国文学专家,对时代的划分与名称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从欧洲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出发,把歌德生活的时代看作浪漫主义时代。在他们看来,不仅荷尔德林、让·保尔或者克莱斯特属于浪漫主义作家之列,而且歌德和席勒也是浪漫主义大家族的成员。歌德被称为古典的浪漫主义诗人。其根据是赖内·韦勒克(Reine Wellek)为欧洲浪漫主义统一性所提出的三个标准:富有诗意的幻想力;自然和它与人的关系;带有运用景象、象征和神话的风格。[5]
德国之外的西方学者之所以把歌德和席勒看作浪漫主义者,有其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不难看出,他们的观点植根于德国浪漫派的理论和德国学者的论述。为了提高德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也为了替已摆脱法国古典文学形式束缚的时代文学辩护,继赫尔德之后,施莱格尔兄弟积极发展浪漫主义文艺的概念。奥·威·旋莱格尔从风格类型上对古典的和浪漫的这对概念加以区别,指出前者植根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后者源出于基督教的中世纪;前者是形象的,一目了然的,后者是音乐的,美丽如画的。据此,他于19世纪初曾称歌德为浪漫主义先驱。随后,让·保尔(《美学入门》,1804)和黑格尔(《艺术哲学》,1826)也都把歌德和席勒的创作归并入浪漫主义文学。1820年,海涅把歌德和他本人的老师奥·威·施莱格尔称作“我们两位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我们最伟大的造型艺术家”。但是后来的德国文学评论就很少或不再把歌德和席勒称为浪漫主义者了。
不管怎样,在德国,尤其是当今,以浪漫主义为歌德那个时代的名称是行不通的。1976年,民主德国文艺评论家京特·哈通在一次国际性的德国文学讨论会上明确表示:“从德国文学史的观点出发,一个拓宽的时代概念,‘浪漫派’,即除‘浪漫派’诗人外还得包括歌德和席勒以及让·保尔、荷尔德林和克莱斯特,那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个拓宽的概念(‘浪漫主义’),起初大概在英国出现,具有文学史的综合内容,并且也因为它(联系到德国文学)包括从歌德的早期作品到三月革命时期的整个时代。”[6]
第四种意见主张“古典文学和浪漫派”并列为时代名称。这是个折中方案,也许是最佳方案。现在有些德国文学史(如原民主德国人民与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德国文学简史》)已接受了这一主张。这个方案之所以比较容易被采纳,就是因为它比较切合当时德国文学发展的实际,顾及了古典文学与浪漫派并存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同时也因为它具有较广泛的统一性,即它能把同时代更多的作家作品囊括进去。让·保尔、荷尔德林和克莱斯特等的流派属性虽尚存争议,但他们的作品都与古典派与浪漫派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当然,这个双重概念的时代名称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因此它也不时遭到非议,包括遭到非德国的西方学者的抨击。尽管如此,接受这一主张的人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