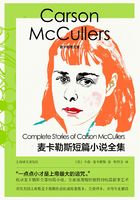
第3章 西区八十号的庭院
直到春天我才开始对住在正对面房间里的那个男人产生兴趣。整个冬季的那几个月,隔在我们中间的小院非常阴暗,面对面的小房间的四面墙壁也给人一种私密感。天气寒冷窗户紧闭时,所有的声音似乎总是会变得低沉和遥远。天经常下雪,朝窗外看时,我只能看见顺着灰色的墙壁纷纷落下的白色而寂静的雪花,窗台上被雪蒙上的牛奶瓶和带盖子的食品罐,或许还有黑暗中从紧闭的窗帘后面透出的一丝亮光。这段时间,我记得只瞥见过几次对面的这个男人的不完整形象——结着霜的窗玻璃后面红色的头发,伸出窗外拿食物的手,朝小院里张望时一闪而过的平静而困倦的脸。我没有怎么去注意他,同样我也没有注意这栋楼里住着的另外十来个人。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也没想到我会对他产生之后的那些想法。
去年冬天我要忙的事情太多了,连朝窗外看的时间都没有。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次来纽约生活。另外,我还需要想办法找到并保住一个上午打零工的机会。我经常想,假如你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却不能把自己打扮得看上去更年长一些的话,你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难找到工作。不过,假如我是四十岁,我也会这么说。总之,现在看来那几个月是我迄今为止过得最艰难的。上午打工(或找工作),下午上学,晚上自习和读书——另外,在这里,我人生地不熟。有一种奇怪的饥渴,我怎么地都无法摆脱,既是对食物的渴望,也渴望着其他的东西。我忙得没有时间在学校交朋友,我从来没有如此孤独过。
深夜,我会坐在窗前读书。家乡的一个朋友有时候会寄来三四美元,让我从这里的旧书店购买一些他在图书馆找不到的书。他会来信索要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或者《第三工具》[14]之类的书,以及马克思、斯特雷奇[15]和乔治·索尔[16]等这样一些作家的书籍。他现在必须待在家乡帮忙养家,因为他的父亲失业了。他现在是汽车修理工。他本可以找到办公室的工作,不过汽车修理工工资更高,而且钻到车底仰面躺在地上时,他有机会仔细考虑并精心计划一些事情。书寄给他之前,我会先研究一番,而且,尽管我们只是简单地谈论里面的许多事物,有时候却会有那么一两句话,能让我原先的一知半解变得清晰明确。
这样的谈论也经常会让我躁动不安,于是,我就久久地凝视窗外。现在想想似乎有些奇怪,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这里,而那个男人却在另一边的房子里呼呼大睡,我根本不了解他,更不在意他。深夜,小院很暗,加上一楼的房顶上盖满了积雪,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死寂的永远不会苏醒的深坑。
春天渐渐来临。我不懂自己为什么总是对事物刚开始发生变化时的样子不敏感,不能察觉空气更加温暖了,阳光更加强烈了,已照亮小院和它四周的房子。薄薄的黑灰色的块状残雪消失,正午的天空已经一片蔚蓝。我只是注意到可以穿羊毛衫而不用穿外套了,注意到外面的声音正变得十分清晰,开始打扰我阅读了,注意到每天早上照在对面大楼的墙上的阳光已经十分明亮了。可是,我忙于应付工作、学业以及业余时阅读书籍所产生的躁动。直到某一天早上,当我发现大楼里的暖气已经关闭,便站起来从敞开的窗户朝外看时,才意识到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说来也奇怪,正是到了那时,我才第一次清楚地看见对面那个红头发的男人。
他跟我一样站在窗边伸头朝外看,两只手扶着窗台。初升的太阳直接照在他的脸上,我感到震惊:他离我这么近,我能如此清晰地看到他。在太阳的照耀下,他的头发闪闪发亮,它从额头往上翘起,通红,似海绵般蓬松。我发现他嘴角圆润,蓝色的睡衣下的肩膀挺拔健壮。他的眼皮微微下垂,不知为何,这让他看上去既精明又沉稳。就在我注视他期间,他进去了一会儿,然后拿着几棵盆栽植物回来,把它们放在窗台上的阳光下。我俩离得很近,在他侍弄植物,小心翼翼地触碰根和土时,我能清楚地看见他那双干净而粗壮的手。他一直反复哼唱着三个音符——这组音符更多地是在表达一种幸福感,而非某种旋律。这个男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让我觉得我可以整个上午就这么站着注视他。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抬头看了看天,深吸一口气,然后又进屋去了。
天越暖和,事物的变化越大。住在小院周围的所有住户把窗帘向后拴住,好让房间透透气,大家还把床挪出来紧靠着窗户。如果你能看到别人睡觉、穿衣和吃饭,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尽管你并不知道他们姓啥名甚。除了那个红头发的男人,我还开始不时地去注意其他人。
那个大提琴手的房间跟我的正好成直角,她上面住的是一对小两口。因为我经常在窗边,因此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的一切尽收眼底。我知道这对年轻夫妇很快就要有孩子了;而且,虽然女的看上去并不很健康,他们还是挺幸福的。另外,我还对那个大提琴手时好时坏的状态了如指掌。
夜晚,当我不阅读的时候,我就会给老家的那个朋友写信,或者在那台我离家来纽约时他送给我的打字机上把偶然间涌入脑海的一些想法打出来。(他知道,我可能要打一些学校里布置的作业。)我记录的那些东西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只是,想办法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对我是有好处的。纸上有很多地方都用×做了记号,也许还写了类似这样的句子: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不可能长久存在,因为它们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世间唯一的罪恶,或者,经济学课上坐在我边上的那个男孩因为没有外套就得整个冬天都在羊毛衫里面塞上报纸,这是不公平的,或者,我知道并能始终深信不疑的东西是什么?当我坐着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对面的那个男人,就好像他总是莫名其妙地跟我内心的想法密切相关——似乎他或许知道该怎么解决那些困扰着我的问题。他看上去是那么冷静和自信。当小院里开始出现那一次的纠纷时,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就是那个可以把它摆平的人。
大提琴手的演奏惹怒了众人,尤其是住在她正上面那个怀孕的女孩。那个女孩非常紧张,似乎过得很艰难。她身体臃肿,脸庞枯瘦,一双小手纤细得跟麻雀的爪子似的。她把头发紧贴着头皮往后梳,看上去就像个孩子。有时候,如果琴声特别响,她就会恼怒地朝着大提琴手的房间弯下身去,差一点就要大声地叫她停止。她的丈夫看上去跟她一样年轻,而且,你能看出来他们十分幸福。他们的床紧靠窗边,两个人经常面对面盘腿而坐,有说有笑。一次,他们就那样坐着吃橘子,并把橘子皮往窗外扔。风把一块小橘皮吹进了大提琴手的房间,于是她就对着楼上尖叫,让他们不要把垃圾扔给别人。年轻的小伙子大声笑着,故意让楼下的大提琴手听见,而女孩则放下吃了一半的橘子,不愿再吃了。
这一幕发生的时候那个红头发男人也在场。听了那个大提琴手的叫喊声后,他还是久久地注视着她和那对年轻夫妇。他一如往常,就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身穿睡衣,神情放松,什么也不做。(下班回家后,他很少再出去。)他看上去慈祥善良,因此在我看来,他希望阻止租户间的紧张关系。可他只是看着这一切,甚至都没有从椅子里站起来,可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听见人们相互间大喊大叫让我焦躁不安,而不知怎么地,那天晚上我感到疲倦并十分紧张。我把正在阅读的马克思的著作放到桌上,然后看着这个男人,想象着他的情况。
我认为大提琴手是五月一号才搬进来的,因为我记得整个冬天都没有听见她练琴。傍晚时分,阳光照进她的房间,把钉在墙上那些看似照片的东西照得分外明亮。她经常出去,有时候会有某个男人来看她。白天的晚些时候,她会拿着大提琴面对小院而坐,她的双膝分得很开,这样她就能骑在乐器上,她把裙子掀到大腿,这样裙缝就不会绷得太紧。她的乐声质朴,演奏懒散。演奏时,她似乎进入了某种痴迷的状态,脸上却是一副害羞的样子。她似乎总有长筒袜需要挂在窗户上晾晒(我看得很清楚,因此我分辨得出她有时候只洗袜底,既保护了袜子,又省去了麻烦),有些早上,窗帘的绳子上还系着一个花哨的小玩意儿。
我觉得对面的男人不仅很理解大提琴手,也理解院子里的其他人。我觉得,他处事不惊,比大多数人都懂得多。也许,这种感觉就源于他神秘的微微下垂的眼皮。我不清楚真正的原因。我只知道,看着他、想着他,我的感觉真好。晚上回家时,他会带回一个纸袋,然后小心地从里面拿出食物来吃。接下来,他会穿上睡衣,在房间里做一些运动,然后就一直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直到半夜。他是料理家务的好手,他的窗台从不凌乱。他每天早上都会打理那些植物,阳光照耀着他苍白但健康的脸。他经常用一个看似洗耳球的橡皮球很细致地给它们浇水。我从来就猜不准他白天干的是什么工作。
大约在五月底,小院里又有了变化。妻子怀有身孕的那个年轻人开始不再定时去上班了。你可以从他们的脸色判断出他已经失业了。早上,他在家里待得比平时晚,他会从依旧放在窗台上的一夸脱容量的瓶子里帮她把牛奶倒出来,以确保在变质前她能把牛奶全部喝完。晚上,有时候,其他人睡着以后,你还能听见他在低声说话。夜深人静时,他会大声地说你听好了,声音之大足以吵醒大家。接着,他会压低声音,对着妻子开始一番低声而急切的长篇大论。她几乎不发一言。她的脸似乎越来越小,有时,她在床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小小的嘴巴半张着,像个睡梦中的孩子。
学期结束了,不过我继续待在城里,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每天五小时的工作,我还想参加暑期课程班。因为不用去上课,我见的人比以前还少,待在家里的时间也更多了。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弄明白,那个年轻人开始带回家一品脱而不是一夸脱牛奶,并最终在某一天带回仅仅半品脱意味着什么。
看见一个人挨饿时你会是什么感受,这个很难说清楚。你看,他们的房间跟我的只隔了几码,因此我没办法不去想他们的事。起初,我不愿意相信所见到的一切。这并不是远在东区的分租房,我会这样对自己说。我们住在城里相当好,或算得上中等的地段——西区八十号。的确,我们的院子很小,房间也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梳妆台和一张桌子,而且,我们跟分租房里的人一样彼此离得很近。但是,从街上看过来,这些房子很不错;两个入口处都有小厅,地面是看似大理石的材料,另有一部电梯让大家不需要费力地去爬那六级或八级或十级楼梯。从街上看,这些房子显得几近富裕,因此里面不可能有人挨饿。我想说:他们的牛奶减到平时四分之一的量,看不见他吃饭(他每天晚饭时间出去,弄点三明治回来给她吃),这并不表明他们在挨饿。因为,她整天那样坐着,除了我们当中有些人用来存放水果的窗台以外,她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仅仅是由于她马上就要生孩子,有一点失常而已。因为,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有时候还对着她叫喊,声音听似有些哽咽,也仅仅是由于他性情乖戾。
一番推理之后,我总是会朝那个红头发的男人看过去。很难解释我对他的这种信任。我不知道那时自己能指望他做什么,但一直有这种感觉。回家后我不再阅读,却经常坐上好几个小时观察他。有时我们的目光会相遇,此时,其中的一个就会把目光转向别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都能互相看见对方睡觉、穿衣、度过下班后的那些时间,不过却没有人说过话。我们住得太近,近得能把食物扔进对方的窗户,近得用一把机关枪就能在瞬间把所有人统统杀死。然而,我们仍然像是陌生人。
不久,年轻夫妇的窗台上再也没有牛奶瓶了,男的会整天待在家里,他的眼圈是棕色的,嘴巴呈一条纤细的直线。每天晚上你都能听见他躺在床上说话的声音——总是从那声响亮的你听好了开始。整个院子里只有大提琴手没有表现得为此事而感到紧张。
她的房间就在他们的正下面,因此她也许没见过他们的面孔。现在,她练得更少,出去得更多了。我前面提到的她的那个朋友每天晚上都在她这里。他矮小精悍,看似一只猫——矮小的个头,油光发亮的脸,大大的杏核眼。有时候,整个小院都听得见他们的吵架声,而且,不一会儿他就出去了。有一天晚上,她搬回来一个充气男人,整条百老汇大街都有这样的充气人出售——长长的气球做成身体,圆形的小气球做成头,头上画着一张露齿而笑的嘴巴。它的身体是亮绿色,绉纸做的腿是粉色,而纸板做的脚则是黑色。她把这玩意儿拴在窗帘绳上,于是,一阵微风吹来,它便摇摇摆摆,慢悠悠地旋转,笨拙地甩着绉纸做的腿。
到了六月底,我觉得再也不能住在这个小院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红头发的男人,我早就搬走了,而且是远在最终摊牌的那个夜晚到来之前。我没有办法学习,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炎热的夜晚。大提琴手和她的朋友开着灯,那对年轻夫妇家的灯也是开着的。我对面的那个男人穿着睡衣坐着,一直朝院子里看。他在椅子边放了一个瓶子,偶尔会把它放到嘴边。他的双脚搭在窗台上,因此,我能看清他弯曲的脚趾。喝多了以后,他就开始自言自语。我听不清他说的话,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一阵不太响亮但高低起伏的声音。然而,我感觉他或许是在谈论小院里的这些人,因为在吞咽的间隙,他会环顾所有的窗户。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只要我们能听清,他所说的就能帮大家摆平一切。可不管怎么用心听,我还是一句都听不懂。我只是看着他那粗壮的喉咙和平静的脸,即使是有些醉醺醺,他那张脸也照样流露出其内在的智慧。什么结果也没有。我永远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哪怕他的声音能高那么一点点,我或许能了解到很多东西。
一个星期以后就发生了这件事,它让一切都有了一个了结。一天夜里,肯定是两点钟左右,我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声音吵醒。所有的灯都关掉了,四周漆黑一片。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里传来的,当我细听的时候,我禁不住全身颤抖。声音并不响亮(我的睡眠不好,否则它根本吵不醒我)但夹杂着一种兽性——亢奋而急促,介于呻吟和惊叫之间。我突然想起,以前曾听到过这种声音,不过那是在很久以前,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走到窗边,从那里听上去,声音似乎来自大提琴手的房间。所有的灯都关掉了,天气温暖,夜色黑暗,没有一丝月光。我站在那里往外看,试图想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在此时,只听见那对年轻夫妇的房间里传来叫喊声,这声音让我终生难忘。原来是那个年轻人,他说的每个字里都暗含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声音。
“闭嘴!楼下的婊子,闭嘴吧!我真是受不了——”
当然,我马上明白原先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了。他说了一半就停住了,院子马上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没有吵闹后原本会出现的那种“嘘”声。有几户开了灯,但仅此而已。我站在窗边,感到十分恶心,全身颤抖不止。我看着对面那个红头发男人的房间,几分钟后他打开了灯。他睡眼惺忪地看着整个小院。做点什么吧,做点什么吧,我想对着他叫喊。不一会儿,他拿着一个烟斗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并把灯关掉了。甚至在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之后,炎热的空气中依旧有他的烟草味儿。
那个夜晚之后,事情就开始变成现在这样了。那对年轻的夫妇搬走了,那间房子一直空着。那个红头发的男人和我都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待在家里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大提琴手那个看似矮小精悍的朋友了,她只会拼命地练琴,总是非常用力地把弓从弦上推过去。每天清晨,当她去收那些挂在窗户上晾晒的胸罩和长筒袜的时候,她总是一把把它们抓进去,然后转身背对窗户。那个充气男人依旧荡悠悠地悬挂在窗帘绳上,依旧慢慢地在空中旋转,咧着嘴微笑,发着亮绿色的光芒。
就在昨天,那个红头发的男人也永远离开了。现在是夏末,通常是人们搬家的日子。我看着他打包所有物品,尽量不去想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到马上就要开学了,想到需要列出的一大串阅读书目。我注视着他,仿佛他是个完全陌生的人。他似乎比这么久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兴,一边打包行李一边哼着小调,他抚弄了那些放在窗台上的植物好一会儿,才把它们拿进去。就在离开前,他站在窗边最后一次看了看整个庭院。在强烈的阳光下,他依旧一脸淡定、目不斜视,不过,他的眼皮下垂得几乎完全闭合,强光在他鲜艳的头发周围形成一个模糊的圈,浑似一个光环。
今晚,关于这个男人我想了很长时间。我一度开始给那个远在家乡当汽车修理工的朋友写回信,可是我改变了主意。原因是这样的——很难跟任何人,包括我的朋友,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如果要真正谈及这个话题,对于他的很多事情我却一无所知——他的名字、工作,甚至是他的国籍。他未曾做过什么,而且,我甚至不是确切地知道自己曾期待他做些什么。我不再像当初那样认为他能给那对年轻的夫妇带来什么帮助。当我回想当初关注着他时的情景,我想不起来他曾做过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如果要对他进行描述,除了头发以外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总的来说,他跟成千上万的其他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不管听上去有多么奇怪,我还是觉得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能改变很多事情,能让它们一一得到解决。而对于这类事情,有一点我需要声明——只要我觉得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