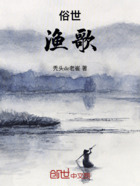
第1章 缘起
天还没亮透,雾就把整个世界裹了起来,像一层怎么也捅不破的厚棉被,捂得人心里发闷。老张头站在船头,看着这片雾,手里的烟袋锅子一闪一闪,那火星子在雾气里明明灭灭,就像他这一辈子,起起落落,没个定数。
老张头是个渔夫,祖祖辈辈都在这片芦苇荡里讨生活。听老辈子人说,他家先祖在大明的时候,那可是跟在太宗皇帝朱棣跟前的大红人。可谁能想到,风水轮流转,满清入关,一家人就逃到了这芦苇荡,过上了靠水吃水的日子。老张头还被叫做小张的时候就知道一句老话,穷不出三代,富不过五服。不像他爹,天天翻来覆去念叨老祖宗的那些事儿,好像靠着这点念想,就能把日子过回从前似的。
芦苇荡里的鱼多得数都数不清,叫得出名的,叫不出名的,都在这水里头游着。渔民也多,多得就像这芦苇荡里的芦苇,密密麻麻。有的人一辈子都住在船上,除了上岸买点生活必需品,就一直在这水上漂啊漂,好像这水就是他们的根。淮河两岸,这样的渔民到处都是,他们没有地主的剥削,说起来倒是自己的主人,可这自由的背后,是数不清的难处。
今天是赶集的日子,老张头猛吸了一口旱烟,烟从他的口鼻里喷出来,和这清晨的雾气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他把船靠了岸,一只脚跨出船舱,动作有些迟缓,就像这雾气一样,透着一股子懒洋洋的劲儿。他把抽完了的旱烟磕在地上,用脚碾了碾,火星子灭了,他的心里也空落落的。
从岸边到村子还有四里多路,岸边的湿气重,不是打鱼的人家,谁也不愿意住在这。老张头的爹,就是因为这湿气,后半辈子都被风湿折磨着。老张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几条鱼,都是三五斤重的,鱼还活蹦乱跳,在竹篓里扑腾着,可他知道,自己的鱼不好卖。不像坟头李,那张嘴就跟抹了蜜似的,死人都能说活了。
“哟,老张,今儿个鱼不错啊,活蹦乱跳的,看着真招人稀罕。郑三姐,您瞅瞅我这鱼,刚从芦苇荡里捞上来的,鲜得很呐!啥?白不白?这是黑鱼,它可白不了,白了那可就出怪事喽!来一条?哟,瞧我这记性,郑三姐买鱼向来都是成对的,对不住对不住。”坟头李那响亮的叫卖声传了过来,老张头听着,心里一阵羡慕,又一阵无奈。
“鱼哟,新鲜的鱼哟!”老张头也扯着嗓子喊了一嗓子,声音在雾气里传出去,没多远就散了。他的叫卖声,和坟头李比起来,就像秋天里的一片落叶,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
“唉哟,我的张哥哟,你这么卖鱼,等你卖完,我卖出去的鱼都下锅喽。哟,宋老师,买鱼回去给媳妇坐月子煲汤吧?便宜点?那肯定行!老师可是咱国家的栋梁,不容易。”坟头李一边卖鱼,还一边和周围的人唠着嗑,那场面,热热闹闹的。
老张头在一旁,看着坟头李的生意红红火火,自己的鱼却少有人问津。他心里着急,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卖了好半天,鱼才卖得差不多了,最后还便宜处理了一条鳃都不动的鱼。他攥着手里那点微薄的钱,心里一阵酸涩,这钱,好像比被地主剥削的那些人还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拖着步子往家走,脚步蹒跚,就像一个被生活抽干了力气的人。
他想起自己的儿子张波,不愿意住在船上,嫌船上空气腥,湿气大,还讨厌吃辣椒。本来他媳妇是一直陪着他在船上的,可儿媳妇挺了大肚子,当婆婆的,总得去照顾,要不然,旁人该说闲话了。
倒是没有多久后的一天夜里,一家人包括老张头正好也在,正一起吃饭。
“老婆子,看儿媳妇肚子像是有双生胎吧,你有咱小波那时候哪有这么夸张?”
“让你找大夫把把脉你还舍不得那两个子,跟我说不着,我又不是大夫。”
“哎哟,哎哟!”突然传出了儿媳妇的呼喊声,张波惊慌,预产期将近,恐是腹中的小儿不安分想要见见世面。老婆子让老张头赶紧去请接生婆,老婆子在里面为儿媳妇的生产做足准备。
今日的老张头还差了两条鲫鱼没卖出去,屋子里鱼腥味和逐渐漫开的血腥味水乳交融,却满是生命的气息。油灯在土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儿媳妇的呻吟声忽高忽低地从布帘后传来。张波攥着发潮的衣角在堂屋里打转,隔着苇席帘子能听见他媳妇指甲抠进土坯墙的沙沙声,得亏是在这土屋子,虽说墙缝里钻着干冷的穿堂风,总比船板下汩汩的水声以及河面上随时阵阵的湿冷的阴风要强。
婴孩的啼哭声刺破了长空的宁静。老张头站在屋外,手里的烟袋锅子早已灭了火,老张头仍吸着烟嘴似是咂摸着味却忘了续火。屋里传来接生婆沙哑的吆喝声:“热水!再端盆热水来!”老婆子掀开帘子探出头,额头上挂着汗珠子,脸上却堆着笑:“老头子!是个带把儿的!”老张头的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摸出火石重新点上烟,火星子在夜色里一跳一跳,映得他皱纹里的阴影更深了。芦苇荡的风裹着水腥气扑过来,他忽然想起自己爹临终前的话:“咱老张家就像这芦苇,看起来是一茬接一茬,却只是空长了许多罢了。”
屋里又响起第二声啼哭,比头一个更细弱,像刚出壳的小水鸟儿。张波从堂屋冲出来,鞋都跑丢了一只,手里还攥着那条没卖出去的鲫鱼:“爹!您当爷爷了!俩!”鱼尾巴在他手底下扑棱,甩出的水珠溅到老张头裤腿上,洇出几点深色的痕迹。
“听见了。”老张头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去把鱼搁灶台上,熬汤。”他说话时眼睛望着远处黑黢黢的芦苇荡,那里有夜鸹子叫了两声,声音像钝刀划破砧板上的鱼肉。
接生婆撩开帘子出来,围裙上沾着暗红的印子。她接过老张头递的铜钱,掂了掂又退回两个:“双生子按规矩该给双份,可你们家……”话没说完,眼睛往土墙裂缝里钻的冷风瞟了瞟。老张头硬是把钱塞回去:“该多少是多少,不能亏了神灵。”
后半夜起了雾,跟清早那阵一样稠。老张头蹲在船头补网,手指头被梭子磨得发亮。老婆子抱着裹蓝布襁褓的孙子过来,孩子小脸皱得像晒干的鱼鳔。天边隐隐的泛起蟹壳青,坟头李的吆喝声已经飘过半个村子。老张头看着竹篓里剩下的那条鲫鱼,鱼鳃微微翕动,他伸手把它抛回河里,像是嫌弃,更像是救赎。
雾更浓了,稠得像化不开的米浆。老张头望着那条鲫鱼甩尾消失在墨绿色的河水中,水面荡开的涟漪转眼就被雾气吞没了。嘬了口烟,浊浊地吐出,像是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两个小不点一张一合着嘴巴,发出清脆的声响,张波媳妇儿侧头看着自己的骨血,笑得很甜,仿佛刚才受尽折磨的不是自己,而是张波,是其他毫不相干的人。
阵阵的冷风吹的刺骨,土屋周围满是泥泞,张波一深一浅的往前探着脚,七里外的付家坡是媳妇儿的娘家。出了村的路要好走许多,乌鸦“啊~啊~”地叽喳着,张波跺着脚,缩了缩脖子。七里地,对交通纯粹依靠脚或者牲畜的年代,也就是半个多钟头的事。天蒙蒙亮,村子里零星的点起了灯。
“砰砰砰!”“砰砰砰!”
“报丧啊!哪有这么敲门的!”屋子里传来声音,紧接着是窸窸窣窣开门的声音。
张波缩着脖子站在门槛外,岳父那张阴沉的脸在门缝里一点点扩大。门开处,屋里的油灯光被挤得忽明忽灭,投在岳父沟壑纵横的脸上,更显得他神色不善。他堵着门,粗布棉袄松松垮垮,眼神像冰锥子一样扎在女婿冻得通红的脸上。
“怎么搞的,这时候来?天还墨墨黑!”岳父的声音带着被咚咚敲门的愠气,压得很低,却像刀子在磨刀石上刮蹭。
“爹……”张波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厉害,声音也似乎被冰冷的空气冻成了冰,“生了,生了!您当姥爷了!”
岳父眉头紧锁,鼻子里哼了一声:“生了?生了就生了,婆娘家谁不生娃?值当鸡还没叫就火烧屁股似的来报信?”他数落着,喷出的呼吸都带着冰碴和鄙夷。
张波那冻僵的手下意识地攥了攥裤管,那里被没卖掉的鲫鱼甩湿的地方早已冻硬了。他心里那点初为人父的喜悦,被岳父劈头盖脸的责问浇了个透心凉。他想起临出门时爹蹲在船头沉默补网的样子,想起屋里微弱灯火下两个皱巴巴的小脸,还有那条鱼——老张头最后扔回河里的那一条。
“爹,不是……”他努力挤着声音解释,“是龙凤胎!宁宁她生了俩!我赶紧来告诉您一声……”他急急地补充,“都平安,都平安着呢!”
“俩?”他声音里的尖利消减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屋里的油灯光线似乎亮了些,斜斜地照在他侧脸上,那深刻的皱纹被光影点缀得更深了。他沉默了几息,那沉默让门外的寒意更重了,乌鸦在远处的老槐树梢又“啊——啊——”地叫了两声。
“……宁宁……还好?”岳父的声音低沉下去,先前那股冻人的愠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绷紧的、试图藏匿什么的生硬。
“好着呢,好着呢!”张波冻得发麻的舌头似乎活泛了一些,赶忙强调,“就是累坏了,两个娃都……都红通通的,哭声挺亮堂!”他那句“红通通”说得有点心虚,但这会儿他只觉得必须把场面说得喜庆些,才衬得上“龙凤呈祥”四个字。
岳父没吭声,堵着门的身体却微微动了动,向屋里让开了半步。一股混着柴火烟、陈旧棉絮和一丝油腥气的暖意从门缝里涌出来,瞬间扑了张波一身。老爷子却没让他进屋的意思,就那么站着,侧身对着他,目光落在院子角落堆放杂物的草棚阴影里。
张波僵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脚上那只冻得发硬的鞋底碾了碾门口结了层薄霜的泥地,发出轻微的嚓嚓声。“爹您去看看不?”
岳父扯了扯嘴角,憋出了一句“进来吧”
门在张波身后发出“吱呀”一声轻响,沉重地合拢,隔绝了门外浓重的寒气和乌鸦断续的嘶鸣。暖意混杂着复杂的陈旧气味包裹了他,却没能立刻驱散他骨子里的寒冷和心头的滞涩。
岳父背对着他站在狭小的堂屋里,油灯的光把他佝偻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怪,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屋角的阴影里堆着农具和破烂,角落里似乎还蜷缩着什么东西,也许是柴草,也许是鸡笼。
“坐吧,灶口暖和点。”岳父没回头,生硬地扔过来一句,听不出喜怒。他指了指火塘边一个小木墩。他自己则走到屋里,摸索着,窸窸窣窣的,似乎在里面翻找东西。掏出了一盒新火柴,划拉着了旱烟“等天再亮些吧”
门外天空渐渐泛起了一层浑浊的白,像是水底浮起的鱼肚皮,灰白色的光影浸润了窗纸,透进一丝冰冷的亮。屋里的动静也多了些,老婆子窸窸窣窣地忙碌起来,动作迟缓却略带着些急切。她佝偻着腰,从墙角木柜里拉出米袋子,米粒洒落几颗在泥地上;又抖开面袋,面粉沾得她袖口一片雪白。十来斤的红枣装在磨秃了边的竹筐里,红皮在昏光中泛着亮;一斤半的红糖用油纸仔细包着,暗的发黑,却带着红糖特有的绵甜气味。老岳父也动了,他摸索着装了一大袋子的旱烟叶,那袋子粗布织的,鼓鼓囊囊像个塞满了风的口袋。老人扶着拐杖,拐杖杵在地面发出沉沉的“笃笃”声,仿佛每一步都在丈量人生的路途。
张波怔怔站着,寒气从脚底往上钻,手也早冻麻木了,心倒是热乎乎的。他如梦初醒,赶紧弯下腰去,一把将那些米、面、红枣和红糖全揽进自己怀里。东西沉甸甸的,压得他本就冻僵的胳膊直打哆嗦,那袋旱烟叶尤其硌人,像揣了块冰疙瘩。他抱着这些物什,身子弓得更低,像是要用这点份量压住心里的慌与喜。
鸡鸣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一路无话,却是五味杂陈。
远远地,老张头家门口挤上了一堆人,“爹,您看,村子里都晓得了,都来道喜呢”张波说着,右眼皮却跳了跳。岳父皱了皱眉,猛吸了一口烟,吐出来的烟却是散的很快。
远处老张头家门口那堆模糊的人影,随着张波抱着满怀东西和岳父走近,渐渐清晰起来。人群里嗡嗡作响,大多是村子里的婆娘们,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夹杂着几声刻意压低的议论“听说了没?没啦!”“哎哟喂,可惜了这龙凤胎,刚生下来呢,就没了娘”
张波一征,枣子散落了一地,走地鸡啄着落在地上的米面,点着头赞同着人群中的那些话。那堆攒动的人模糊成了影子,在湿冷的雾霭里扭曲着形状,嗡嗡的议论声像无形的针,狠狠扎在张波的耳膜上。岳父略带着喜悦的脸瞬间煞白,点燃的旱烟从他哆嗦的手里滑脱,“啪”地摔进泥泞里,火星溅灭,只剩下袅袅一丝绝望的青烟。
“没了……娘?”张波的嘴唇翕动着,重复着听到的话,每一个字都想着天气一样冰冷刺骨。呆愣愣的站立着,像是一个死机了的机器人,重复根本不存在的那个指令。
岳父像是被无数个巨大的锤子猛然击中,整个人佝偻下去,那双原本聚如鹰隼的眼睛霎时空洞,死灰一片。他什么也没说,喉咙翻动的,仿佛是那点呜咽被冷的冻住了。他踉跄着,歪歪扭扭着,用一种近乎行尸走肉般的步伐,挤进了了老张家那扇门,摔进了那个满是新生命气息、却残留着一丝着死亡气息的土屋。
张波还维持着站立的姿势,僵在原地。他听到屋里骤然爆发出沉闷的撞击声,然后是岳父压抑不住、从喉咙深处撕扯出来的、濒死野兽般的嚎哭,那哭声比乌鸦的悲鸣凄厉百倍,击碎了门板,冲散了屋外的嘈杂。混合着的,是两个新生儿稚嫩而无助的啼哭,一曲悲怆的交响乐。
张波如梦初醒,像是被瞬间抽干了力气,双腿一软,“噗通”跪倒在冰冷的泥地里,十指深深抓进冻土里。刚解冻般的喉咙发出一声,是一种被撕碎的、悠长的、沙哑的抽噎,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散落的红枣滚到他身下,被碾进泥里,化作春泥更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