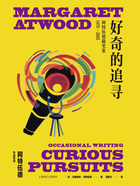
第一部
1970—1989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之后我回到多伦多,做了两年的大学职员——约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同时和一家叫做阿南西印刷屋的小型文学出版社合作。为他们编辑了诗歌书目;另外还编写了《生存》,一本关于加拿大文学写作的书——这个主题之下第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作品。这本书在当时的加拿大立刻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引发争议”。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加上持续不断的女权主义热潮,让我经常遭受攻击。
在那之后不久,我和同是作家的格雷姆·吉布森一起住到了一个农场里。我们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劲头十足地干着农活,虽然没能收获多少经济回报。我们有一片很大的菜园,自制了许多罐头,甚至还腌起了德式酸菜,这项活动在家附近的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开展。我们养了奶牛、鸡、鹅、绵羊、鸭子、马、猫和狗,还有孔雀和其他动物。其中许多都上了餐桌,欢乐的美餐不时被装着自制啤酒的瓶子在地窖里爆炸的声音打断,还有格雷姆的孩子们询问盘子里装的是不是他们的苏珊。
一九七六年我们有了一个孩子,到了要上学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孩子每天得要坐两个小时的校车,于是便搬进了城里。这段时期我们在爱丁堡住了一年,因为格雷姆是苏格兰—加拿大作家互访项目的加拿大代表。爱丁堡超越了伦敦,一年之中发生了卡车司机罢工、通往伦敦的火车隧道塌方,和一次除雪车罢工。我们吃下了许多抱子甘蓝、三文鱼,还有羊毛。
这段时间我第一次在德国办了巡回售书。我们还在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节的路上绕了一个大圈,带着十八个月大的孩子去了伊朗(沙阿在八个月后就会被推翻)、阿富汗(在我们离开之后大约六个星期就爆发了内战),还有印度,我们在泰姬陵参观的时候,孩子在阿格拉的一家酒店里学会了爬楼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于我而言是积极活跃的,事后证明对全世界也意义重大。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苏联似乎稳如泰山,理应还会延续很长时间。但它已在阿富汗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损失惨重的战争,而柏林墙也在一九八九年轰然倒塌。一旦根基脱落,一些权力架构的崩塌之迅速着实令人震惊。但在一九八〇年,谁都不曾预见到这个结局。
我的这段时期开始得相当平静。我正在尝试,第二次且并不成功的尝试,写作那本后来会成为《猫眼》的书,同时也在构思《使女的故事》,虽然对于这后一部作品我是能不碰就不碰:它看起来实在太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故事设想也太离奇了。
我们一家这会儿住在多伦多唐人街的一栋排屋里,房子翻新的时候把许多内墙都拆除了。我没法在里面写东西,因为屋里太嘈杂了,所以我会骑着自行车往西走,去葡萄牙区,在另一栋排屋的三楼写。《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集》刚刚编完,书页散满了整个楼面。
一九八三年秋天,我们去了英格兰,租下一栋诺福克的牧师住宅,据说客厅里有修女的鬼魂出没,餐厅里有一位快活的骑士,厨房里则是一个无头女人。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不过倒确有一位快活的骑士在找洗手间的时候迷了路,从隔壁的酒吧误闯进来。电话装在屋外,是投币式的,电话亭同时还兼做土豆储藏室,我会攀爬越过这堆蔬菜,来处理——比如说——收录在这本书里的厄普代克作品评记的校订工作。
我在一间渔夫小屋改造成的度假屋里写作,和阿加牌暖气机以及已经动笔的一部小说艰难搏斗。这让我第一次生出了冻疮,但小说只能被迫放弃,我发现自己把时间线搞得一团糟,找不到解决的出路。
随后我们去了西柏林,在那里,在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开始写起了《使女的故事》。我们游历了一些地方,去了波兰、东德,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地方帮助形成了书里的氛围:极端主义独裁统治,身上的装束再怎么不同,恐惧和沉默的气氛是共同的。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写完了这本书,当时我在塔斯卡卢萨的亚拉巴马大学担任访问讲席教授。这是我在自动打字机上按正确的格式写的最后一本书。每完成一章,我就会把原稿传真给我在多伦多的打字员,认认真真地重打一遍,我还记得传真机即时传送的魔法让我惊奇不已。《使女的故事》一九八五年在加拿大出版,一九八六年在英格兰和美国面世,在引发其他各式骚动之外,还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
一九八七年我们有一部分时间在澳大利亚度过,在那里,我终于能够认真着手写作《猫眼》,这部让我苦苦挣扎了好几年的小说。书中风雪最大的场景是在悉尼温暖和煦的春天里完成的,还有笑翠鸟在后门廊上啾啾叫着要人喂汉堡。这本书一九八八年在加拿大付印,一九八九年在美国和英格兰出版,也同样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就是在这个时候,萨尔曼·拉什迪被下达了处决的教令。当时又有谁知道,这第一阵风吹草动,日后掀起的不是什么波澜,而是一场飓风呢?
在这期间,《使女的故事》在电影行业的幽曲小道里逐渐推进,最终呈现出了完整的形式,由哈罗德·品特编剧、沃尔克·施隆多夫导演。电影一九八九年在东西柏林首映,正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还能买到墙体的碎片,有颜色的那种更贵一点。我去参加了庆祝活动。同样的那些守卫,在一九八四年的时候还是那么冷冰冰的,现在却咧嘴笑着,和游客交换雪茄烟。东柏林的观众对电影的反响更好。“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一位女士轻声对我说。
我们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在一九八九年那段短短的时间里。从无可能变成现实的奇观场面让我们多么的头晕目眩。对于即将踏入的勇敢新世界,我们的想法又是多么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