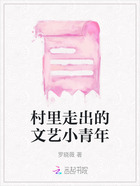
第1章 随笔
在热闹繁华的公园一角,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说正在火热进行,演讲者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路人纷纷被吸引驻足。就在这时,一位身形佝偻的老爷爷迈着蹒跚的步伐缓缓走来。
他头戴一顶略显破旧的尖顶帽,身上那件外套更是打着好几个补丁,一看就是历经岁月沧桑。老爷爷一出现,演讲者瞬间停下了滔滔不绝的话语,满脸敬重地快步走到他面前。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碰撞出别样的火花。演讲者操着一口浓浓的乡音,恭敬问道:“您可是老李先生?”老爷爷微微点头,声音沉稳有力:“正是,我便是老李。”演讲者接着又好奇地问:“听闻您是青山村人人敬仰的智者,不知是不是真的?”老李淡然一笑,回应道:“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我也便受着了。”演讲者忍不住笑了笑,调侃道:“‘智者’这词儿,感觉挺特别的,用在人身上还真是少见,真是稀奇得很呐!”老李听后,捋了捋胡须,认真地说:“人就是人,不管叫什么,都该保持善良的本心。”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而我呢,作为一个热衷于在晚餐前散步的文艺青年,每天都会来到公园。我尤其喜欢在河边的长椅上静静坐下,隔着朦胧的河水,眺望对岸的风景。这座城市特有的浓雾,像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岸边肆意弥漫。我惬意地倚着桃木手杖,手托下巴,目光直直地望向远方。只见那雾气从对岸蜿蜒而来,越来越浓,好似一条巨龙,缓缓地从那五层楼高的街区席卷而过,最后在一片朦胧中渐渐隐匿了身影。就在这如梦似幻的时刻,天空中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洒下微弱的光点。紧接着,三层、四层、五层的建筑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依次点亮了电灯,星星点点,煞是好看。我起身,缓缓地朝着住处走去。
每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老李和那些演讲者的故事总会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在那被昏暗灯光和雾气笼罩的地方,便是老李曾经生活过的青山村,那里仿佛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探寻。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老李早已离开了人世,那位演讲者或许也已化作一抔黄土。然而,青山村却依旧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一位忠诚的守护者,见证着岁月的变迁。老李居住多年的老房子,更是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顽强地保存着往昔的模样。自1788年建成的青山街以来,这房子历经无数次主人的更迭,却始终坚守着最初的记忆。老李去世后,一群热心的文学爱好者自发地行动起来,他们四处收集老李生前用过的器物、家具、图书等物品,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一摆放在各个房间,还特意为那些对老李充满敬仰和好奇的人,提供了随时参观的便利。说到和青山村有着深厚渊源的文人墨客,那可真是数不胜数。
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曾经的老周、稍晚些的老吴、与老李同时代的老郑,还有备受瞩目的老谢。老郑的家与老李的家相距不远,据说,老李曾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搬家,还特意前往老郑家拜访,这段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老李的文献之中。此外,老郑还曾送给老李的妻子一尊老谢的雕像,这一佳话也在文人圈中广为流传。除了他们,老艾居住过的房子和老罗曾经的庄园,也都坐落在靠近河边的小街上。只是可惜,这些地方早已物是人非,换了新的主人,如今已无法供人参观。唯有老李的旧居,依旧敞开怀抱,欢迎着每一位前来探寻文学奥秘的人。只需支付六毛钱,你便能踏入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老宅,自由地穿梭在各个房间,感受老李曾经的生活气息。青山路在河岸边的小路上悠然地往南拐去,而老李的房子就静静地坐落在路右边的中间位置,门牌号是二十四号。几乎每一天,我都会隔着河流,在那如梦如幻的雾气中深情地凝望着青山村。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大步跨过桥梁,来到了那座心心念念的老宅前,咚咚咚地敲响了那扇神秘的大门。提及老宅,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寂静、冷清的画面,脑海中也会浮现出雅致、古朴等美好的词汇。然而,老李的老宅却截然不同,它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柔弱之感,而是充满了一种独特的硬朗气息。那是一座四层的方形建筑,稳稳地矗立在离街道极近的地方,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坚定与执着。不管是那突兀的突出部分,还是略显内敛的凹陷之处,都直直地挺立着,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远远望去,它就像是从一座大型工厂的烟囱根部直接切下来,然后巧妙地加上了天花板,又精心装上了窗户,独特的造型让人过目难忘。这座房子,可是老李历经千辛万苦才寻觅到的。他从遥远的北方乡村而来,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住所,他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往西寻过,往南找过,甚至在城北的郊外也苦苦寻觅过,可始终未能找到那座让他心动的房子。直到最后,他偶然来到了青山路,当第一眼看到这座房子时,他的内心竟涌起了一丝犹豫。他向来对世间万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可在面对这座房子时,却一时没了主意。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知自己的妻子,听听她的想法。妻子很快便回复道:“你说的那两座出租房都各有千秋,并无不妥之处。若是你想等我进城后再做决定,那咱们便先将此事搁置一旁;倘若到时必须做出抉择,你便自行拿主意吧。”老李在文学创作上可谓才华横溢,见解独到,可在挑选房子这件事上,却似乎格外依赖妻子的意见。在夫人进城之前,他也只能无奈地等待着。四五天后,家中的琐事终于处理完毕,夫人也顺利抵达。随后,夫妻二人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寻觅之旅。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反复的权衡,他们最终还是认定“青山路”的这座房子最为合适。
1954年6月10日,这对新婚夫妇满心欢喜地搬进了这座充满希望的房子。夫人之所以钟情于这座房子,或许是因为它独特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她,又或许是在众多选择中,这座房子是最契合他们心意的。总之,这座外形酷似烟囱的方形房子,热情地迎接了这对幸福的新人。此后,老李便在这座充满故事的房子里,潜心创作,写下了关于老朱、老蒋等历史人物的经典作品,还毅然拒绝了老钱介绍的高薪工作,过上了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此刻,我满怀期待地站在这座方形房子的石阶上,用力地敲打着那威严的狮面门环。不一会儿,屋里便走出一位身形富态的五十多岁老妇人。她笑容满面,热情地将我迎了进去,似乎一眼就看出我是前来参观的游客。老妇人动作娴熟地很快拿出一份类似名单的东西,礼貌地询问我的名字。我回忆起在这座城市逗留的那段日子里,我曾四次踏入这座房子,也四次在这份名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一次,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书写。
我努力地想要把字写得工整漂亮些,可不知为何,写出来的字依旧歪歪扭扭,难以入目。我好奇地翻开前面的名字,惊讶地发现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这一发现让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原来我竟是第一个以中国人身份前来参观的人,这种独特的体验让我倍感荣幸。老妇人微笑着示意我跟她走,我轻轻打开左边的门,走进了那间朝向街道的房间。据老妇人介绍,这里曾经是客厅。屋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物品,墙上挂满了精美的画和珍贵的照片,其中大多都是老李夫妇的肖像。
在后面的房间里,有一个据说按照老李的设计精心打造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塞满了书籍。这些书种类繁多,有的晦涩难懂,仿佛藏着无尽的奥秘;有的略显无聊,让人提不起兴趣;有的陈旧泛黄,散发着岁月的气息;还有些则让人望而生畏,根本无法读懂。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摆放着为纪念老李八十岁生日而特意铸造的银牌和铜牌,奇怪的是,却唯独不见金牌的踪影。这些带着“牌”字的物件,都显得格外坚硬,仿佛能抵御时间的侵蚀,长久地保存下去。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得到它们的人的生命却是如此短暂,不禁让人感叹岁月的无情。接着,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上了二楼。这里同样有一个巨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籍。和楼下一样,有许多让人望而却步的难懂之书,也有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奇书籍,甚至还有些书因为尺寸奇特,根本无法插进书架。我闲来无事,仔细数了数,这里一共有135本书。
据老妇人说,这个房间曾经也被用作客厅。在这个房间里,还珍藏着老冯送给老李的信件和上面颁发的勋章,想必这都是因为老李撰写的关于老蒋的精彩传记而获得的殊荣。房间里还摆放着老李妻子曾经用过的床,那床造型笨重,毫无装饰,显得朴实无华。导游这个职业,似乎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有着相似的特点。就像眼前这位老太太,她正滔滔不绝地逐一讲解着室内的每一件物品,那熟练的程度,就算是经过五十年专门训练的资深导游,恐怕也难以望其项背。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毫不费力,仿佛这些故事早已深深烙印在她的灵魂深处。更有趣的是,她那流利的口才还带着独特的起伏和节奏感,就像一首优美的乐章。然而,这富有韵律的语调却让人有些困扰,如果你只是单纯地专注于听她的调子,就会发现根本听不懂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时不时地打断她,询问她具体的内容,可后来实在觉得太过麻烦,便索性不再追问,心里想着:“你说你的,我就自己看自己的吧。”于是,我便采取了这样一种“各自为政”的态度。老太太似乎丝毫不在意我的反应,依旧自顾自地讲着她那些烂熟于心的故事,脸上没有丝毫的厌倦之色,也没有任何懈怠的迹象,依旧认真地讲述着何年何月何日发生了何事,仿佛在向我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
我走到东侧的窗户旁,好奇地伸出脖子,想要一窥附近的景象。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大约十平米左右的花园,四周被高高的石头围墙紧紧环绕,整个花园的形状依旧是方方正正的,仿佛与这座房子的风格完美契合。方形的元素在这里随处可见,仿佛已经成为了这座房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不禁想起老李的面容,他的脸可绝对不是方形的,倒更像是悬崖中间某一部分突然塌陷,然后倒伏在草原上的奇特模样。而他的妻子,看上去则像是一根精致的韭菜,有着独特的韵味。再看看此刻正在给我做导游的老婆婆,她那圆圆的脸庞,活脱脱就像一个白白胖胖的馒头,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正当我看着老婆婆的脸暗自思忖时,她又开始背诵起某个特定年月日发生的故事。我无奈地再次从窗户探出头去。
老李曾经说过,从后窗望出去,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树株、翠绿的田野,以及其间点缀着的陡峭的红色屋顶。微风轻轻拂过,眼前的景色明朗而又令人心旷神怡,仿佛一幅绝美的画卷。我满心期待地想亲眼看看那茂盛的树叶,眺望那片充满生机的青翠田野,于是迫不及待地从后窗探出头去。然而,现实却让我大失所望,我接连探了两次头,却什么青色的东西都没有看到。右边是一座房子,左边也是一座房子,前方依旧是一座房子,四周被房子包围得严严实实。天空中,一片铅灰色的乌云沉重地压着,就像一个患有重病的人,无精打采地低垂着,让人心情莫名地压抑。我失望地把头缩了回来,从窗子里退回到房间。而导游依旧在兴致勃勃地欢快朗读着某年某月某日的后续故事,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的失落。
老李还曾说过,看向城那边,眼中所见仅仅是城隍庙和天主堂的高塔顶端。其他那些如同幻影般的宫殿建筑,在带着煤灰的云影中渐渐消散,悄然隐去,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可如今,“城那边”早已成为了过时的话题。在今天,站在青山村看向城那边,就如同坐在自己家里审视周围的事物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也就是在近距离地审视自己眼前的认知。然而,老李当年却并不认为自己住在城里,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住在乡下,在他的心中,自己正远远地凝视着城中心那座宏伟的大寺庙,仿佛那里藏着他的梦想与追求。
我怀着一丝执念,三次伸出脖子,努力地看向他所说的“城那边”。可是,城隍庙早已不见踪影,天主堂也消失在茫茫的城市之中。如今,成千上万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数十万的人在其间忙碌穿梭,几百万的嘈杂声音交织在一起,重重地立在我与那些曾经的标志性建筑之间,飘荡着,移动着,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将过去与现在彻底隔开。1834年的青山村和今天的青山村,简直是天壤之别,让人不禁感叹岁月的巨大变迁。我无奈地再次缩回了脖子,此时,老太太默默地站在我的背后,静静地伫立着,仿佛也在感慨着时光的流逝。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上三楼。当我不经意间看向房间的角落时,冷冷地看到老李的床铺横在那里。青色的窗帘静静地垂着,空荡荡的床榻显得格外孤寂、昏暗,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那张床的材质不知是何种木料,但其雕工只是笨拙而朴素,除此之外,毫无特色可言。
看着这张床,我仿佛能感受到曾经横卧在上面的人的种种遭遇,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伤感。床边是他平时用过的浴桶,那浴桶此刻如九鼎般尊贵地摆放着,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曾经的重要地位。虽说是浴桶,其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桶罢了。忽然,我抬头一看,墙上挂着据说是他临终时所戴的石膏面具。没错,就是这张脸,那独特的轮廓,仿佛带着岁月的痕迹,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想象着他曾在这座像烟囱一样高大的浴缸里洗澡,然后躺在这简单的床榻上,在漫长的四十年里,不断地吐出那些让人烦恼的唠叨声,我的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张脸。而老婆婆那口无遮拦的话语,此刻在我耳边就像听到横滨人打招呼般清晰,仿佛将我拉回到了现实之中。婆婆微笑着对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上去看看吧。”此时的我,仿佛已经将城市的尘土与喧嚣远远地抛在了地面,独自坐在五重塔的塔顶,沉浸在一种宁静而又超脱的氛围之中。可是,耳边突然传来的“我们上去吧”的催促声,让我瞬间有些疑惑,难道这房子还有更高的地方吗?短暂的思索后,我还是答应了上去。随着一步步往上走,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悄然升起,那是一种对未知的好奇与期待。当我终于来到四楼时,心中充满了迷茫与无知,但同时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高兴。与其说这是高兴,倒更像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心头涌动。这里是阁楼,我抬头看向天花板,只见两侧低矮,中间却高高隆起,宛如马鬃的形状,在最顶端的脊梁上,有一个玻璃窗,阳光透过它,洒下明亮的光线。从这间阁楼射进来的光线,都是从头顶直接射入的,头顶上,仅仅隔着一层玻璃,便与广阔无垠的天空相通,眼前没有任何遮挡物,让人感觉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原来,这间房间是老李亲自精心经营建造的。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将这里建成,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书房。待在这里,我才真正深刻地意识到,我的计划与他的想法是如此的截然不同。这里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又寒冷刺骨,实在不是一个舒适的居住之所。导游用她那特有的朗读语气说到这里时,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她那圆圆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仿佛在询问我对这里的看法。我默默地轻点了点头,心中对老李的敬佩之情又增添了几分。那么,老李为何会在这座接近天空的房间里辛苦地经营建造书房呢?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性格如电光般迅速的人,思维敏捷,行事果断。然而,他的神经质却仿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包围圈,任何细微的噪音都无法逃过他的耳朵,严重干扰他专心写作。那些钢琴声、狗叫声、鸡鸣声、鹦鹉叫声,所有的声音都像一把把尖锐的刀,无情地刺激着他那异常敏锐的神经,让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深渊。最终,他在这座四楼的天花板下,找到了这个既接近天际又远离人群的住所,希望能在这里寻得一片宁静的创作天地。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在屋顶正上方建一个二十尺见方的房间。这是通过加建双层墙壁、天花板上取光以及巧妙通风的设计来解决问题,以确保没有任何不便。即使全天下的鸡都同时发出叫声,我也可以安然无恙。”如他所期盼的那般,书房在花费了两千日元后,基本按照他的设想完美完工,并且取得了预期的绝佳效果。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就在他以为终于能摆脱噪音干扰,安心创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障碍再次悄然降临。的确,钢琴声消失了,狗吠声也停止了,鸡鸣声、鹦鹉的叫声也都如他所愿不再响起。但那些在低层时未曾注意到的寺庙钟声、火车汽笛声,以及从遥远地方传来的、无法知晓来源的世界声音,却像恶魔的诅咒一般紧紧追赶着他,依旧像往常一样无情地折磨着他的神经。声音,这个看似平常的东西,在英国,曾让作家卡莱尔无比困扰,而在遥远的东方,它也曾是叔本华心中的噩梦。叔本华曾无奈地感慨:“康德曾写过关于活力的理论,而我反而打算写一篇反思活力消亡的文章。物体碰撞的声音、敲击的声音、物体滚动的声音,都是活力的滥用,我因此每天都在痛苦中度日。听到这些声音却没有任何感受的人,若听了我的理论定会笑。但若世上有不理解逻辑、思想、诗歌、艺术的人,那就一定是那些遗忘了这些美好事物的人。他们的脑袋结构粗糙,领悟迟钝,毫无疑问,这正是其根本原因。”卡莱尔与叔本华,这两位身处不同地域却同样被声音折磨的智者,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最独特的一对搭档。
当我正沉浸在这些思绪中时,那个老太婆冷不丁地问我,“怎么样,要下去吗?”每下一个楼层,就有一种逐渐接近尘世的感觉,仿佛之前构建起来的冥想世界的外壳正被一点点剥落。当我终于走到底层,倚在最下方的栏杆上,眺望街道时,那种超凡脱俗的心境瞬间消失,我又变回了那个普普通通、为生活奔波的凡人。引导者面不改色,语气平淡地说,“请看看厨房吧”。厨房位于街道下面,从我站立的地方还需再下五六阶楼梯。这里是现在引导我的老妇人的住所,角落里有一个大灶炉。
最后,我被从厨房门引导到庭院。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个四四方方的平地,这里根本看不到像样的树木和草坪,显得有些荒凉。根据老奶奶的回忆,曾经这里有娇艳的梅花,也有繁茂的葡萄,她还说这里以前还有结满果实的胡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