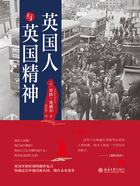
导读
《英国人与英国精神》收录了乔治·奥威尔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写的纪实散文和评论文章,包括《狮子与独角兽》《北方和南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和《英国人》。这些文章抓住了帝国由盛到衰时英国人的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呈现了战争和时代剧烈变迁中英国人的彷徨与希冀,以及奥威尔对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反思。
奥威尔有着典型英国人的爱好和钟情的生活方式。他坦言喜欢养花种菜、英式烹调、印度红茶、壁炉烛光和舒适的椅子,不喜欢城市、喧嚣、汽车、收音机和现代家具。他出身于不那么富裕的中产家庭,曾与上流阶级的子弟一起接受教育,还在英国殖民地做过警察,穷困潦倒时“洗过盘子,当过家庭教师”,在书店打过短工。境遇好转后,他靠写作维持生活,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还开过一家杂货铺,上过战场,受过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威尔曾多次报名参军,皆因体检不合格遭拒,后参加国民自卫队,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主持对印度广播,并参与了有关战争的报道,也担任过工党刊物《论坛》的文学编辑。这些丰富的阅历和社会生活体验为他展现文学才华以及探讨社会巨变下的英国国民性和文化特色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根基。
他毫不掩饰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自豪,“写英语乃至说英语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英国文化独一无二,它表现在“丰盛的早餐、阴沉的礼拜天、雾蒙蒙的城镇、蜿蜒的道路、绿色的土地和红色的邮筒。它有着自己专属的味道”。然而,他最推崇的还是绅士风度,尤其是英国普通人的文雅举止,如人群自觉排队,汽车售票员待人和蔼可亲,警察无须配枪等。他不讳言英国人的伪善,“绅士风度夹杂着野蛮”,尤其是在帝国问题上的两面派做法:“八十年来,英国一直在人为阻碍印度的发展,部分原因是担心,如果印度工业过于发达,就会与英国发生贸易竞争,部分原因是落后民族比文明民族更容易管理。”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是伪善的,“印度需要的是在不受英国干涉的情况下制定自己宪法的权力,但需要与英国保持某种伙伴关系,以获得军事保护和技术支持”。他没能免俗,也爱“凡尔赛”,自诩英国统治者不像德国那样鼓吹纳粹诉诸种族主义,英国媒体不像法国媒体那般无耻地直接收钱办事,英国语言的使用也不像美国那般随意。
他是纯粹的英国人,有着基于经验主义的惯性思维和带有讽刺挖苦意味的幽默。他喜欢莎士比亚,也喜欢狄更斯。他深受毛姆“直截了当讲故事”的影响,以记者在场和纪实的手法,精准再现立体多样且具特色的英国日常生活细节,如“刚吃完腌鱼和喝过浓茶的一家人围坐在煤火旁”的温馨场景。他把对日常经验的描写置于广阔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历史中,将个人焦虑与对现代化的反思结合起来。他“不认为工业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且不可避免的丑陋。……北方的工业城镇很丑陋,因为它们建造的时候,钢铁建筑和除烟方法还不发达,且那时每个人都忙于赚钱而顾不上其他事情”。他观察到英国人的素质在提升:“就外表来说,富人和穷人的衣着,尤其是女性的衣着,差异已经很小了。至于居住条件,英国仍然有贫民窟,这是文明的污点。”但他也指出,“英国人改掉粗野生活的习惯还不到百年的时间”。他那不经意的叙述指出了现代文明之原罪,带出了对责任与良知、个体独立性与群体权威之间张力的拷问:“在我写作时,高度文明的人类正驾机飞过头顶,想要杀了我。他们不是对我个人有恶意,我对他们也没有。俗话说得好,他们只是在‘履责’而已。”奥威尔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焦虑跃然纸上。一方面,他承认“作家只有摆脱政党标签才能保持正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除非你不断努力把自己的个性抹掉,否则是无法写出什么可读的东西来的”。因此,他清醒地指出,英国北方和南方的地域歧视只是源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如此。在他看来,无论地域歧视还是民族主义理论都是资产阶级塑造的一种思维习惯,是“自欺欺人的权力欲望”的说辞,这类说辞缺乏是非善恶的判断和自我的反思,对国际问题常常采取内外有别的“双标”;受到欧洲大陆思潮蛊惑的英国知识分子转向权力崇拜,比普通民众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俘获;依然坚守基督教伦理的普通民众只遵从“正派”做人的道理,认为“强权不是公理”。
奥威尔秉持的是柏克(Edmund Burke)开创的舆论引导的基调,认定现代英国文明是“微妙妥协的结果”,“是奇特的混合体,是真实与幻觉的结合,也是民主与特权的结合”。英国的民主不是“像有时候看上去的那样是个骗局”,因为统治者始终不敢对民意“装聋作哑”。民主虽然不完美,但有半个面包总是好过没有面包。“虽然法律既残忍又愚蠢,但至少不会腐败。”他批判英国的现状,为的是英国的未来,“狮子与独角兽”的题目来自英国国徽,直抒胸臆,“在预测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中英国应扮演的角色前,最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英国是啥”。他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有产者顽固不化,“一个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却被等级制度的鬼魂所困扰”。有产阶级的合法性逐渐削弱,无力应对纳粹的挑战,导致英语堕落蜕化,生育率下降,教育成了中产阶级最大的开销,“他们知道‘高层有的是空间’这句话不是真的”,他们仅仅是希望工作稳定,并“为他们的孩子争得一个公平的待遇”。知识分子从未被统治者当作“高贵者”,“几乎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被授予任何一个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在其1947年所写的《英国人的未来》中,奥威尔指出,只有在生育率提升,社会更加平等,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情况下,英国才能在未来世界中保持住大国的地位。
他对工人阶级始终抱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试图超越自身的阶级地位和知识分子身份去接触底层社会,从工人阶级那里吸取文化养分。在他看来,对抗资本主义、克服阶层固化弊端、战胜法西斯的希望在于工人阶级。他说工人阶级的家庭不像资产阶级的家庭那么暴虐,因为“工人的脖子上没有磨盘般沉重的家族名声负担”。工人阶级不虚伪做作,“如果你给一个工人一样他不想要的东西,他会告诉你他不想要;一个中产阶级则会接受这个他不喜欢的东西以避免冒犯你”。他通过“小店主”一词,暗示追逐私利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常常与国家利益相悖。他认同的爱国主义是人们“对某个地方、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热爱”。爱国主义既是英国的民族底色,是英国人的“本能”,更是英国人的“无意识”,“英国的民族团结远远强于阶级对抗”。虽然各个阶层都是爱国的,但情感强弱有别。中产阶级比上层阶级更爱国,工人阶级的爱国情感最强烈。奥威尔希望通过革命改变资产阶级的特权,实现权力的根本转移,但他心目中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将爱国主义与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并不必然导致流血,也不意味着一个阶级的专政。在他看来,英国赢得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与英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互为成就的,“不搞社会主义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不赢得这场战争,社会主义也无法建立起来”。他相信“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更有可能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是要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一个自由与平等的大同世界,人权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通过这些纪实报道性的文字,奥威尔借助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左派政治立场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他提醒国民,在珍视和继承国家特色的同时,更要反思自身制度的弊端,客观摆正变化世界中的本国地位。他称赞工业化带来的进步和国民素质的提升,也批判了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与有产者的虚伪和顽固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