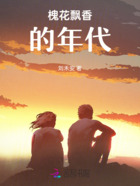
第19章 暗流
一九八五年九月的一个清晨,程卫东被急促的拍门声惊醒。窗外天刚蒙蒙亮,姜晓兰还在熟睡,怀里的程梅咂着小嘴,发出轻微的鼾声。
“程厂长!快开门!“是大刘的声音,压着嗓子却掩不住惊慌。
程卫东轻手轻脚地下床,刚拉开条门缝,大刘就挤了进来,满身烟味混着汗臭,眼睛里布满血丝:“质监局的人来了,带着封条!说我们消防不合格!“
程卫东的睡意瞬间消散。他回头看了眼卧室,姜晓兰的轮廓在晨光中微微起伏。随手抓起外套,跟着大刘冲进秋凉的晨雾中。
厂门口停着三辆吉普车,十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在往大门上贴封条。领头的男人四十出头,腆着肚子,胸前别着“安全检查员“的塑料牌。
“王队长,“程卫东认出了质监局的熟人,“这是...“
“程厂长,对不住了。“王队长避开他的目光,递过一纸公文,“突击检查,消防通道堆放杂物,配电室违规使用明线,立即停产整顿。“
程卫东接过文件,手指微微发抖。这些所谓“问题“在乡镇企业里再常见不过,往常都是限期整改,何至于...
“赵科长特别关照的。“王队长凑近低语,呼出的热气带着烟味,“你得罪人了。“
赵德才。程卫东咬紧后槽牙。自从拒绝那批劣质钢材,他就料到会有这一出,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多久?“程卫东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至少半个月。“王队长瞥了眼正在拍照取证的同事,“等复查合格才能复产。“
工人们陆续赶来,聚在厂门外窃窃私语。老马师傅蹲在路边,粗糙的手指一遍遍捋着花白胡子;几个年轻学徒茫然地抱着工具袋,像被抛弃的小兽。
“东哥!“张建军骑着自行车疾驰而来,车把上挂着装满资料的布袋。他今天本该在省城上课,显然是连夜赶回的。看到封条,他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右脸的伤疤愈发显眼。
“周教授那边...“程卫东刚开口。
“带来了!“张建军拍着布袋,“新传动装置的设计图,效率能提15%!但需要...“他的声音低下去,“需要重新开模试产。“
程卫东胸口发闷。这正是最糟糕的时机——停产意味着无法完成外贸订单,违约金会压垮刚有起色的厂子;但若错过这次技术升级,产品很快会被市场淘汰。
“先开会。“程卫东拍拍手,“全体到李婶家院子集合。“
李婶的院子挤满了人。程卫东站在磨盘上,看着下面七十多张焦虑的面孔。这些都是拖家带口的工人,半个月没活干,很多家庭就揭不开锅了。
“工资照发。“程卫东第一句话就让会计老刘瞪圆了眼睛,“从我的厂长基金里支。“
人群骚动起来。大刘突然站起来:“东哥,咱们可以偷偷...“
“不行!“程卫东斩钉截铁,“违规生产只会给人口实。“他转向张建军,“你继续说技术方案。“
张建军展开图纸,讲解新型传动装置如何减少能量损耗。工人们听得云里雾里,但都被他眼中的光芒感染。程卫东注意到,他的讲解方式越来越像周教授,会用手势强调重点,会在关键处停顿。
“问题是,“张建军推了推眼镜,“试产需要三万块钱,而且...“他犹豫了一下,“得用省钢的特殊合金。“
院子里一片寂静。三万块几乎是厂里全部流动资金,更何况现在原料采购也被赵德才卡着脖子。
“我有办法。“姜晓兰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抱着程梅,身后跟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晨光给她镀了层金边,怀里的婴儿好奇地抓着母亲衣领。
“这位是省报的林记者。“姜晓兰介绍,“想采访我们厂的技术创新。“
程卫东瞬间明白了妻子的意图——舆论造势。林记者已经掏出笔记本,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满院子的图纸和零件。
“程厂长,听说你们自主研发的收割机比苏联原型更节能?“
采访持续到中午。林记者走时,带走了张建军的演算手稿和程卫东整理的“企业发展受阻情况说明“。姜晓兰送他到村口,回来时发现程卫东独自蹲在槐树下,揪着枯黄的草叶。
“梅梅呢?“程卫东闷声问。
“李婶带着。“姜晓兰在他身边蹲下,“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程卫东抬头,看见妻子眼下浓重的阴影。自从程梅早产,她没睡过一个整觉,现在又为厂里的事奔波。
“省儿童医院来了位康复专家,“姜晓兰轻声说,“看了梅梅的情况,建议...“她顿了顿,“建议做三个月强化训练。“
程卫东握紧拳头。上次去省城检查,医生就说过孩子运动发育迟缓,需要专业康复。但当时想着在县里慢慢做,现在...
“要去省城住三个月?“
姜晓兰摇头:“每周三次,当天往返太折腾,所以...“她深吸一口气,“一中王校长说,省城分校缺语文老师,可以借调我半年。“
程卫东猛地站起来,又缓缓蹲下。工厂危在旦夕,妻子要���着病弱的孩子远赴省城,而他却被困在这个满是泥沼的县城。
“去吧。“他最终说,声音沙哑,“梅梅要紧。“
姜晓兰抓住他的手:“可是厂里...“
“我能处理。“程卫东挤出一个笑容,“大不了去找沃罗宁帮忙,他不是说过...“
“程厂长!“张建军气喘吁吁地跑来,“刚接到电话,沃罗宁明天到省城!说要带东欧客商来看样机!“
夫妻俩面面相觑。这本是天大的好消息,可现在厂子被封,样机还缺关键部件...
“我去见他。“程卫东当机立断,“把图纸和样品带上,在省城找地方演示。“
“但停产期间设备不能外运...“张建军提醒。
程卫东眼中闪过一丝锋芒:“那就再造一台。“
夜幕降临,李婶家后院却灯火通明。工人们自发聚集,用从家里搬来的工具加工零件。没有大型设备,就用最原始的方法——老马师傅带着徒弟们手工打磨齿轮;大刘用煤炉加热金属,一锤一锤地锻打关键部件。
姜晓兰抱着程梅,挨个给工人们递毛巾擦汗。婴儿似乎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异常安静,黑亮的眼睛映着跳动的炉火。
“东哥,“张建军凑到正在组装传动轴的程卫东耳边,“刚收到周教授电报,他联系了省钢的郑总工...“
程卫东手上动作不停:“怎么说?“
“愿意特批五吨合金,但需要现金交易,不开发票。“
这明显是违规操作。程卫东抬头,看见张建军眼中的挣扎——这个曾经最守规矩的年轻人,现在也在为工厂铤而走险。
“买。“程卫东咬牙,“用我家的房契抵押。“
凌晨三点,第一台手工组装的传动装置终于成型。程卫东转动试验台的手柄,齿轮发出流畅的“咔嗒“声。工人们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有人甚至偷偷抹眼泪。
“成了!“张建军检查完数据,兴奋地宣布,“效率提升16.7%,超过预期!“
程卫东却注意到姜晓兰靠在墙角睡着了,程梅蜷在她怀里,小手还抓着母亲的一缕头发。晨光微熹中,他看见妻子眼角未干的泪痕。
轻轻抱起女儿,孩子在他臂弯里扭了扭,又沉沉睡去。程卫东凝视着这张与自己相似的小脸,突然做了决定。
“建军,你带样品去省城见沃罗宁。“
张建军瞪大眼睛:“我?可是...“
“你比谁都懂这项技术。“程卫东拍拍他的肩,“我和晓兰送梅梅去住院,三天后跟你会合。“
他转向熟睡的姜晓兰,轻声说:“这孩子需要父母都在身边,至少...至少刚开始治疗的时候。“
张建军郑重点头,右脸的伤疤在晨光中像道勋章。工人们默契地开始拆卸演示装置,小心打包零件。老马师傅不知从哪找来辆破旧的面包车,正在给轮胎打气。
“东哥,“大刘突然从门外跑进来,手里挥舞着个笔记本,“小王在废料堆捡到的!“
程卫东翻开泛黄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钢材规格和金额,每隔几页就有个“赵“字,后面跟着不同数字。最新一页写着:“9.20,给王局三千,封厂事成再付两千。“
“证据有了。“张建军凑过来看,“但怎么用?直接举报会打草惊蛇...“
程卫东合上账本,眼中闪过决然:“先复制一份。这次去省城,我找林记者帮忙。“
太阳完全升起时,面包车满载着零件和希望驶向省城。程卫东抱着程梅,姜晓兰靠在他肩头浅眠。后视镜里,老槐树的轮廓渐渐模糊,树梢上已经能看到零星的金黄——秋天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