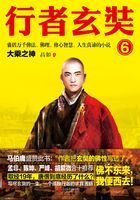
第6章 瑜伽止观的修证
对于这位来自遥远他乡的求法僧,般若跋陀罗深感钦佩,总觉得其旺盛的求知欲似乎没有止境,但他同时也发现了玄奘身上存在的问题,善意地指了出来——
“法师的学问、辩才和悟性都是没话说的,美中不足的是,在修行实践方面用功太少。瑜伽宗本身是非常注重禅修的,因而此宗的行者身体大都不错。我观法师身子单薄,平日里是否花时间做些修习呢?”
玄奘道声惭愧:“弟子也修些瑜伽止观,但用时很少。近些年来一心习经,只盼日后能够回国弘法,普度众生,在修行方面就有些懈怠了。”
“法师的宏愿令人钦佩。只是生命短暂而佛法无边,凡人终其一生也是学不完的,更遑论领悟?况且经典说到底也只是知识层面的东西,犹如指月之指,并不能彻底解决生命的问题。一个修行人,对身体的修炼必不可少。否则,你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越多,就迷失得越深。”
“大师所言甚是。”玄奘看着面前的经夹,长叹一声道,“弟子自幼修习止观,无论是长途跋涉还是静坐思虑都时有法喜在胸。近年来沉迷于各类经典,于佛法方面领悟日深,却不知为何,竟时有迷失的感觉!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有时弟子会忍不住地去想,莫非是波旬居士前来造访了吗?”
“波旬居士不曾来。”般若跋陀罗笑道,“法师只是太注重法理了,以致荒废了禅修。有时间还是依照你所学的《瑜伽师地论》进行次第的修炼吧。想当年,老僧甚至还尝试过各种苦行,都是很有帮助的。”
“苦行?”玄奘惊奇地看着这位老修行,“就像恒河边上的那些苦行者吗?印度人似乎都很重视苦行,玄奘却不信这是通往无上智慧的路径。当年佛陀也是抛弃了苦行才得道的,虽然那六年苦行对于佛陀来说至关重要,但最终还是被他抛弃了。”
般若跋陀罗摇头道:“佛陀所修的苦行不止六年,而是无始劫。我们不是佛陀,如何能与之相比?”
玄奘想了想,点头道:“大师所言在理。玄奘若是没有经历过那段西行之旅,倒也不介意去尝试一下。不过现在嘛,还是不浪费这个时间了。”
般若跋陀罗微笑点头:“是啊,法师走这一段路,便是一场苦行了。你说印度人都重视苦行,其实也不全是。比如顺世外道就追求享乐,以快乐为人生目的。法师听说过他们吗?”
玄奘点头:“弟子进入印度之后,看了许多有关六师外道的书,对于这些教派的基本主张,都略略知道一些。顺世论者否定因果轮回的存在,反对祭祀和苦行,反对一切伦理道德,与佛法可谓背道而驰。不过他们主张种姓平等,这是令玄奘深感钦佩的。玄奘甚至觉得,他们的主张有些类似于我国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
“哦?”般若跋陀罗的眼睛亮了一下,似乎对玄奘的话颇有兴致。他当然不晓得什么是魏晋玄学,只是对那个遥远又神秘的国度感兴趣罢了。
由顺世派,两人自然而然地又谈到了六师外道,般若跋陀罗道:“其实六师外道有两种:一种是形成于佛陀时代的非正统六师,像顺世派、耆那派、不可知论派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是从婆罗门教中分离出来的正统六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致尊奉《吠陀》经典。法师听说过吗?”
玄奘点头:“弥曼差派、胜论派、数论派都属于这一类,那烂陀寺中有这些教派的全部经典。”[1]
般若跋陀罗很高兴:“正统六派中,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便是有关生命价值的诸种学说了。”
“还有令人惊叹的细致严密的知识论、本体论和宇宙论,完美的因明逻辑。”玄奘接口道。
“看来法师还是对知识体系感兴趣啊。”般若跋陀罗不禁笑道。
玄奘也笑了笑:“弟子不能善悟,惭愧。”
般若跋陀罗却不介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道之门,法师也不必感到惭愧。这个世界上有人执着于名,有人执着于利,而法师执着于知识。说到底都是贪欲在作怪啊。老僧只是希望法师能在阅经之余多些体验罢了,须知佛法与世间法最大的不共之处就在于体验。世间的哲学纯粹是比量的产物,是人对世界进行思考的结果。这思考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佛法则不同,它是佛菩萨和瑜伽师们在修行中证悟出来的。”
玄奘信服地点头道:“长者所言极是。当年我师父也曾跟我说过,佛法修行中,观想非常重要。早期部派佛教的典籍中,就有许多禅观方面的内容,包括观地、观水、观火、观不净、观无常、观佛像……还有净土法门的观想念佛和观像念佛,一旦观想成熟后,诸佛菩萨便会随着观想显现,这是从实践中体证唯识。”
般若跋陀罗点头道:“《摄大乘论》中说:‘诸瑜伽师于一物,种种胜解各不同,种种所见皆成立。’修瑜伽止观,无论观想的是什么,在观想成熟时都可显现出来。常人的观想达不到这个效果,是因为心力不够。散乱的心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一旦处于定中,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佛陀才会说:‘置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和拿镜子聚光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似乎并没有太大作用,然而对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说,起心动念便会形成极大的力量。所以说,唯识是禅者们修行的体证。我们修习唯识观,最终是为了证得唯识性,而不是单纯地学习理论。”
玄奘心有所悟,默默地思考着,般若跋陀罗的声音又在他的耳边响起:“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些重要的目的,就像法师的目的是求法一样。而要实现这些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人本身,否则不待完成,生命就已经终结了。而要改变人本身,仅仅依靠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依靠信仰也很值得怀疑,因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没有准备好,信仰是没有根基的。”
“所以老僧希望法师能抽时间做一些瑜伽修炼,这不仅因为法师本身就是瑜伽行派的论师,更重要的是,瑜伽修炼几乎是印度所有哲学和宗教的共有财产,其真正的优势不是知识体系,而是对身体的严格训练,对呼吸和心灵的训练,并且提供次第的修行实践和戒律。这些心智训练和内证功夫非常重要,也是印度各教派的传统。”
听得此言,玄奘心有所感,合掌称谢。
又是一个清晨,雨意盎然的天光将地面照得清清亮亮的,像是夜里刚刚涂好的香油。
师子月早早地来到那烂陀广场的讲坛前,清晨的重露打湿了他的衣襟,他却浑不在意,一心想要看看那位东土法师是何等样人。
原以为自己来得已经算是很早的了,却不承想讲坛前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希望能够占到一个更好的位置。
“果然是个名望出众的讲经师,难怪能将师兄击败……”师子月心中暗暗自语。
他忍不住想起那天,一向辩才无碍的师兄师子光,满面通红地来到他驻锡的大菩提寺,一坐下来就开始诉说自己如何在辩论场上受到东土客僧的羞辱,以致无颜再留在那烂陀寺,只能转到这里讲经。话语间充满了愤愤不平。
师子月自是热情地留住了师兄,他知道师兄的脾气性情,多年修行,依然改变不了那份孤傲和冷峻,这世间怕是极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同时,他也听说过玄奘的名声和传说,很多来自北印度的僧侣居士都曾用钦佩的语气说起这位来自东方的求法僧,如果那些传说不是夸大其词的话,脾气暴烈的师兄败在此人手下也在情理之中。
“那个边地客僧傲气凌人,又有正法藏戒贤的庇护,我想,你肯定不敢去同他辩论!”师兄当时这么说。
师子月很为难,他倒并不在意师兄的激将法,只是从师兄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种渴望,渴望自己前往那烂陀寺,与玄奘一辩高低,为他这个师兄,也为大乘中观学派一雪前耻。
“可是,我并不知道此事的因缘啊……”他心中暗想。
师兄一向对法偏执,这他是知道的,现在又以这样一种惨败的姿态出现在自己面前,显然是受辱过甚。自己该不该去替师兄出这口气呢?
于是他笑着说道:“能够在论辩酬答中战胜师兄的,绝非寻常之人啊。”
师兄不满地哼了一声:“也就那么回事吧。我讲述中百二论,也不过是破斥了他们的‘遍计所执’,对于‘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还是没有提到,他却断章取义地以一句‘一切无所得’来否定所有论述!”
“这么说,那玄奘真是采用了非常规手段才赢得胜利的?”师子月默默思索着,“以师兄的辩才,却被他辩驳得哑口无言,徒众离散,这其中必有缘故。”
转念又想:“我这次因为一个不明不白的理由离开东印度,千里迢迢来到摩揭陀国度夏,正不知是何因缘,却无意间遇到了这种事情,这难道不是佛陀的安排吗?我是否应该听从佛陀的旨意,前往那烂陀寺,向东土客僧挑战,为师兄雪耻呢?”
这样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安顿好师兄后,他便独自一人来到那烂陀寺。
站在寺门前那面巨大的论鼓前,师子月思忖良久,最终还是没有去敲那面鼓,而是选择了径直进入。
他本不是个争强好胜之人,辩论也不见得非得要大张旗鼓不可,还是先了解一下这个声名显赫的外国僧侣再说吧。
他很轻易地通过了门童的诘难,又轻松打探到玄奘的住所。一路上,没有人再来为难他,那烂陀寺的学风一向开放,每天,从各地赶来的求学者、游历者乃至挑战者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寺僧们早已习以为常,只要与自己无关便不去过问。
意想不到的是,他没有在那座漂亮的精舍内见到玄奘,却先读到了《会宗论》,那些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偈语在他眼前逐渐勾勒出一个才华横溢的僧人形象……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快要被说服了。
“不。”他对自己说,“仅凭一部论著不能说明什么!在你亲眼见到这个沙门之前,还是不要先妄下结论的好。”
如今,坐在法台下的师子月静静地等待着,就像当年和师兄一起去拜望恩师一般,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急切地想要见到一个人了……
玄奘在般若跋陀罗大师的指点下,彻夜修习止观,直至拂晓时分。
这本是他自幼常做的功课,即使是在艰苦的西行路上也从未废弃。还记得在恒河之上为性力派教徒所擒,被迫充作人牲时,他端坐祭坛进入禅定,居然上升到了睹史罗宫,面见了弥勒菩萨!那种感觉是如此美妙,令他难以忘怀……
只是进入那烂陀寺之后,这五年来,他全部身心都放在了真经佛典上,对于修行本身倒有些荒废了,心中时常感到不安。如今正好趁便补上一补。
好在他根基上佳,又极具慧根,稍加点拨便受益匪浅。
睁开眼时,他觉得自己似乎休息了很长时间,又仿佛有一股细细的清泉从心中流过,令他神清气爽,浑身上下安适自在。
这种愉悦的感觉真是久违了。
般若跋陀罗在他的旁边盘膝而坐,手边放着一碗准备好的乳粥,微笑着说道:“法师尽享禅悦之乐,可喜可贺。”
“全靠大师教导。”玄奘感激合掌道,“弟子近些年来一直沉迷于书卷之中,如今方知圣典所在,还在于实修实证。从今往后自当学有所宗,由博返约,返璞归真才是。”
般若跋陀罗点头微笑道:“法师果然是有宿慧之人,日后光大佛法,指日可待。”
“玄奘也希望能光大佛法,怎奈能力有限,自度尚且不暇,如何能够化他?”
“无妨的。”般若跋陀罗道,“弘扬佛法是一段极其漫长的道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起点上,所以佛陀才会针对不同根器的人讲说不同的佛法呀。”
“多谢大师开导。”玄奘恭敬合掌。
这时,般若跋陀罗已将那碗乳粥放在了他的面前:“法师不必思虑太多,还是先用斋吧。须知人的身体就像一只渡舟,善待之,尽可能走得长久一些,才有可能走得更远,离彼岸更近。”
玄奘再次合掌,双手接过粥罐:“大师金玉良言,弟子谨记于心。”
辞别长者,玄奘回到那烂陀寺。
天已大亮,直接返回住处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他径直来到法坛处,未及更衣就登坛讲经。
师子月站在人群的后面,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来自异域的比丘。
看他也不过三十多岁的年纪,身材高瘦,一袭半旧的青色僧袍垂落下来,越发衬得他风鉴朗拔,卓然不群。
不知怎的,一见此人,师子月的心中便自然而然地生出一股敬意。
玄奘一步一步走上法台,一直走到法座前转身,合掌向台下大众施礼,随后便轻提衣襟,稳稳地坐了下来,开始今天的法会。
他讲经向来不依文本,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抑或是佛典之外的道理,皆是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对一些艰涩的理论常有绝妙的神解,在座的众人很快就被吸引住了。
师子月细细听来,只觉得这位东方法师肃穆中自有一股威仪,显得那样与众不同。特别是他的声音,具有一股强大的穿透力,自己离得虽远,仍可听得清清楚楚——
“四分说,就是把人心理认识的发生和过程进行总结归类,佛陀先立了‘见分’‘相分’和‘自证分’。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立刻分辨出那是什么,你认为‘看到和分辨出来’是同步完成的,其实错了,这里面有很多的过程。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其实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看、看到、思维’,这就是唯识学精微分析人类动作和思维活动的特点。”
“如果这样的话,‘思维’这一环便是最终的结果了,是不是?”台下有人问道。
“不是。”玄奘回答道,“佛法从来不认为有什么‘最终’,所以,才会再立‘证自证分’,以证明‘自证分’的心理活动。”
“可是,立了‘证自证分’,这个‘证自证分’就又成了最终的结果,还是违背了佛法本旨。是不是还需要再立第五分呢?那样岂不是没完没了了?”
“问得好!”玄奘赞赏地说道,“佛法妙就妙在它是圆融无碍的,‘证自证分’与‘自证分’可以相互证实,如同一个圆圈,所以不用再立第五分。”
“原来如此。”那人心悦诚服地点着头,其余听讲众人也都频频点头。
玄奘的辩证思维令师子月敬佩不已,同时又略觉不服,他想,这些都是瑜伽行派的理论,本身也无甚新奇之处,只怕以前戒贤都曾讲过,为何人们还是听得如痴如醉呢?莫非这东土僧人真有如此强大的众生缘,以至于人们都被他魅力所折服?
讲经时声音传得远、不依文本、说理清晰,对听经者的疑难应对自如、有问必答,且答得十分圆融浅显。这种能力固然很强,却也不足为奇。五印度的很多高僧大德甚至外道论师都具备这些能力。除此之外,这东土客僧还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师子月闭目深思,耳边还回荡着东土法师清越的声音,这声音传得虽远,却似乎并不洪亮,反而透着一股温润与醇厚,恍如山间清流平缓地淌过玉石,既令人舒服,又令人信服……
师子光没有告诉师弟,玄奘于辩才之外还有一种能力,那便是气场。很多论敌站在他的面前会明显地感受到压力,以至于口干舌燥、面红流汗,头脑一片空白。说起话来更是声音发颤、语速加快,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很多毛病……
现在,师子月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沉重的压力和痛苦。
早在来此听经之前,他就已经在心中筹划好了十余条尖锐的问题,准备在玄奘讲经的过程中抛出,挑起一场激烈的论战,也看看这位声名卓著的法师辩才到底如何,究竟有没有真才实学,能不能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征诘?但是不知为何,每次当他想要开口时,都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在心头,令他张口结舌,直至心悸流汗……一直到玄奘讲经结束,他竟始终没有开口发问一次!
法会结束时已接近正午,卢达罗耶牵过大象诃利,室利般摩和摩离多罗两位弟子满面焦虑地站立两旁。
“师父。”一向大大咧咧的室利般摩率先发问,“你昨晚一夜都没有回来,今早为何也不回精舍一趟啊?害弟子们白白担心了一夜!”
玄奘一面抚摸着大青象,一面笑道:“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你们也都是修行人,不好好做自己的修习,替别人瞎操什么心啊?”
“不是弟子自寻烦恼,实在是……”室利般摩说到这里,竟有些说不下去,偷偷瞧了摩离多罗一眼。
“怎么了?”玄奘感觉到了不对,奇怪地问道。
“是这样的,师父。”摩离多罗合掌回禀道,“你昨夜没有回来,有个东印度论师到精舍拜谒。”
室利般摩的脸色变得紧张起来,不由自主地跪下。摩离多罗见他如此,也跟着跪了下来。
“你们到底是怎么了?”玄奘越发觉得奇怪,“东印度论师?哪个国家的?他今天来听经了吗?”
说罢朝身后看了看,那些听经的人已经三三两两地散去,其中有几位正恭敬地向他顶礼合掌。
“弟子留他在精舍内暂住,可他拒绝了。他……他还借走了师尊的《会宗论》……”室利般摩的声音越来越小,垂着头,不敢看师父。
玄奘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的《会宗论》有很多不妥之处,不想再四处张扬了。但是,就算此论被某位论师借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正法藏早已命人大字抄写,悬于三座藏经阁中,这寺中上上下下没读过此论的,只怕已为数不多,两个弟子何至于如此紧张?
显然,此事还另有隐情,绝不单单是把《会宗论》借走那么简单。
想到这里,玄奘温和地说道:“你们两个站起来说话吧。”
“是,师尊。”两人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室利般摩还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你们说的那位东印度论师,法讳为何?”玄奘问道。
摩离多罗垂手答道:“回师尊,他说他叫旃陀罗僧诃。”
“月亮狮子……”玄奘喃喃自语,“莫非是师子光长老的师兄弟吗?”
室利般摩吓了一跳:“师尊你怎么知道?”
“我瞎猜的。”玄奘知道自己猜对了,也终于明白了两位弟子为何如此紧张。
他现在并不想同师子月论师一辩高低,相反,他更愿意同这位中观学派的学者交个朋友,并借他向师子光长老表达自己的歉意。
“这位大师,他人呢?”玄奘边问边在心里盘算着,或许,我该亲自登门拜访才对。
“弟子不知。”摩离多罗道,“弟子原本以为他今日必借法会之机向师尊问难,却不承想他一直没有露面。”
“你们怎知他一定是来找我论战的呢?”玄奘问道。
“这是明摆着的。”室利般摩道,“他是师子光长老的师弟,师子光长老刚刚离去,他就突然来到那烂陀寺,这其中必有缘故。听师兄说,此人在东印度名气极大,特别擅长讲经和辩论。”
玄奘道:“讲经辩论,宣扬佛法,乃是功德无量之事。想当年,佛陀可以用宽广的心胸去接纳众生,对众生取得的一切成就,表示由衷的欢喜和赞叹。你们不随喜他的功德和智慧也就罢了,怎么还胡乱猜疑?”
两个弟子相互望望,一时说不出话来。
“看到别人有功德有智慧,或者仅仅是有好运气,获得了某些世俗与非世俗的成就和快乐,我们从内心为他感到欢喜,这,便是‘随喜’。”师徒三人坐在诃利的背上,朝精舍的方向而去。玄奘趁机向身边的两个弟子讲起普贤菩萨的随喜之愿。
“佛陀曾经说过,随时给人欢喜、给人方便,是很大的功德。《汇集经》云:‘三千须弥可称量,随喜善根不可量。’”
摩离多罗垂着头道:“弟子也曾读过《汇集经》,却一直没有搞明白,为什么随喜会有这么大的功德?一个人,只需要克服嫉妒心理,只是为他人的行为和成就高兴一下,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也未免太容易了吧!”
“你觉得很容易,说明你是有善根的。”玄奘赞了弟子一句道,“有些人或许没有嫉妒心,却不见得就肯随口说些好话,更何况是从心里为他人的成就、功德和利益感到高兴。这不是嘴巴说说就能做到的。嫉妒心没有了,但别的习气还在。否则,为什么你们一听到师子月大师是东印度最有名的论师,就开始担忧起来了呢?”
“弟子以为,他就是来找师父麻烦的。”室利般摩抬头道。
东土法师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或许是玄奘的习气吧,不小心熏染了你们,才会使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原本是要净化内心,使自己的心量等虚空、遍法界,最终契入佛菩萨的甚深广大境界。你们千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那些智慧比自己高的人就一定会伤害自己。”
摩离多罗连连点头,又有些不好意思:“弟子明白了,其实今日师子月大师根本就没来找师父的麻烦,都是弟子自己在那里瞎担忧,连累得师弟也跟着担忧。”
“就是啊。”室利般摩也跟着开朗起来,“说不定他是真心佩服师父,真心来向师父请教的!”
玄奘笑着摇头:“人家是来请教的,还是来论战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尊重别人。当你在欣赏别人、尊重别人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庄严自己、成就自己。这,就是功德!”
说话间,他们已经快要走到住处了,玄奘注意到,院门前的那棵开满蓝色花朵的金香木下,一个中年僧侣正在静静地打坐。
“停一下。”他抬手道。
净人卢达罗耶连忙吆喝着让诃利停下,玄奘从象背上慢慢地爬了下来。
室利般摩赶紧也跟着下来,奇怪地问道:“还未到精舍,师父为何这么早就下了象骑?”
玄奘整了整衣襟,微笑道:“你们说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咱们可不能失礼。”
法会一结束,师子月论师就来到玄奘的住处,一边在树下打坐,一边静候玄奘的到来。
他的心中早已不存辩论之想,但是既然答应了师兄,总该有个交代。
坐不多久,就听到远处花丛中传来一阵有节律的声响,那是衣衫掠过草叶的声音。
抬起头,正看到玄奘沿着花径朝他走来,长衣下摆处沾了些茸团状的胡星草叶,身后跟着两个年轻弟子,再往后是牵着青象的净人。
师子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总能在这个外国比丘身上看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威仪和德光呢?
玄奘走到客僧面前,双手合十,深深一揖:“四海皆是有缘人。大师请到舍下一坐,喝杯茶,去去尘。”
师子月忙起身还礼,室利般摩快行几步,上前打开院门,大家一起踏进蒲草捆扎的篱笆院落。
“这座小院可真漂亮。”师子月边走边说。他的身旁是几棵果实累累的核桃树,树下随意堆放着几块黑褐色的檀木写板,上面纹满了蝌蚪状的花纹,看起来不像是佛经。
“这里是护法菩萨的旧居。”玄奘向他介绍道,“玄奘住在这里,闭目便可得见圣贤之面,受教之余也常常觉得惶恐不安。”
“难怪。”师子月微笑道,“我听了法师的法会,也看了法师所著的《会宗论》,法师是护法菩萨的信徒吗?”
“玄奘还不敢说自己是护法信徒。至于《会宗论》,里面的内容还是稍显偏狭拘浅,玄奘虽为求法,却偏执于法,真是深感惭愧。”
师子月感到一阵意外,他原本以为,玄奘定会挟胜利之势同他辩论一番,至少也会有些自得之意,却不想他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两人踏入客房,一股夹着檀香味儿的凉爽之气扑面而来,让人不由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师子月知道,这是因为房间的一侧挖了冰窖,那烂陀寺十大德的精舍内都有这样的冰窖,用几层厚厚的贝多罗树叶子掩盖着冰块,冷气从里面透出,再加上房屋的墙壁厚达两尺,因而室内显得十分清凉。
至于檀香气味,自然是佛龛前点燃的线香发出的。
玄奘道:“护法菩萨身为瑜伽论师,但在瑜伽行派与中观学派的争执中,并没有一味地偏袒瑜伽一方,而是另外提出中道的看法。他说:‘如是等类随见不同,分隔圣言令成多分,互兴争论各执一边……未会真理,随己执情,自是非他,深可怖畏!应舍执着空有两边,领悟大乘不二中道。’玄奘自以为对中百二论和《瑜伽师地论》已融会贯通,却以自身局狭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佛法,以致引起误解。同先贤相比,当真惭愧无地。”
“法师太客气了。”师子月道,“难道不是我师兄在讲《中百论》的时候,先批斥《瑜伽师地论》的吗?”
其实师子光并没有跟他说这些,但他了解师兄的脾气,对事情的经过多少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两人在屋子中央的白色毛毡上敷座而坐,净人卢达罗耶奉上凉茶,师子月合掌称谢。
玄奘继续刚才的话题:“师子光长老只是脾气性情刚烈了一些,其为人和学问都是极好的。怪只怪玄奘年轻气盛,根性又浅,法执实在是太重了。”
师子月微微一笑:“只怕我师兄的法执更重吧?”
玄奘摇头轻笑道:“我已决定暂离那烂陀寺,去各地游学。还请大师代我向师子光长老表达歉意,就说玄奘年纪轻,多有冒犯,恳请长老容谅一二,重回那烂陀寺。”
师子月吃了一惊:“法师要离开?为什么?”
“玄奘当年曾经发下宏愿,此行要尽自己所能,将大乘佛法完整地传回东土。幸有佛陀护佑,让玄奘来到那烂陀寺,遇正法藏,拜为师尊。每日里畅听大乘佛典,受益匪浅,本不该再存他想。怎奈玄奘生性愚鲁,心中总有些疑难未解,因而有意继续南行,游学五印,广诣大德。”
注释:
[1]形成于笈多王朝时期的婆罗门六派分别是——弥曼差派,吠檀多派,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尼夜耶派。此六派学说虽呈多样性,但都承认《奥义书》中的业与轮回思想,而以脱离轮回为其最终目的。由于各派皆以自派所说为正确教理,因此彼此之间屡有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