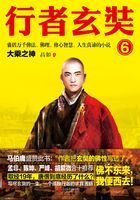
第7章 暂别那烂陀寺
这个计划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尚未向正法藏提出,却对这个初次见面尚不知是敌是友的论师说了,也算是累世的缘法,玄奘心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师子月看着玄奘:“法师意欲离开,当真是为了游学吗?”
“玄奘不打妄语。”
“不是我师兄的缘故?”
“确实不是。早在这次讲筵前玄奘就有此意了,只是当时恰逢雨安居将至,又欲报正法藏传授之恩,这才留下来讲经。玄奘所学尚浅,不能尽窥佛法真谛。加之修为又低,时有不净之心,所以才会与师子光长老发生争论。”
师子月摇了摇头:“佛法如海,我辈又如何能够尽窥真谛?至于学者论辩,各执其理,也未必都是争论。莫非法师这段日子在开讲《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时,遇到了一些疑难吗?”
“疑难原本就有,非讲经时偶遇。”
“比如?”
“比如《唯识三十颂》的释论,玄奘在那烂陀寺见到过八位论师所造的释论,听一位长者说,此论至少还有两个,大概分别在东印度和南印度,不知大师可曾听说?”
师子月点头道:“听说过。只是,法师为何一定要读完《唯识三十颂》的全部释论呢?”
“因为,玄奘所读的这几本释论在阐释和说理上都各不相同。只有读得多了,才能于混沌之中见到真正的法源。就如同盲人摸象,虽不能像明眼人那样得窥全象,然而摸的地方多了,心中的形象便会逐渐地趋向于真实。若只读一两个版本,只会产生误解和执念,执着于自己碰巧摸到的那一点点地方,就以为佛法是相互抵触的,很多争论便由此产生了。”
师子月缓缓点头,因见识少而产生执念,继而产生争论,这样的事情在各个宗派中都有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凡夫的局限。
玄奘接着说道:“其实,佛陀说法的意趣虽各有侧重,但其终极目标和根本意旨却是一味的。玄奘写《会宗论》,也是想透过中观学派与瑜伽行系不同的论理方式,阐发其内在的、本质的共通之处,以消除由于后学者理解上的偏颇而引发的歧见。虽然现在看来,此举实在有些自不量力了。”
“原来如此。”师子月的心中既佩服又有些感慨,想起《会宗论》里的话:空有二宗同一法源,绝不会互相抵触。所谓辩难,只是研究法的人本身的局狭造成,绝不是法的本身有缺失。
这些话有什么不对吗?他现在已经明白,玄奘在《会宗论》里并没有以牙还牙地驳斥《中百论》,更没有对师兄本人有过半句不敬的言语,相反还很欣赏。一个能够真心欣赏别人,特别是欣赏对手的人,其内心已经接近佛陀。他是快乐的,也是满足的,为何师兄就如此地放不下,反而弄得自己不快乐呢?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话题,交谈中,师子月越发感受到玄奘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坦荡谦和,从容自在,完全没有师兄所说的那么傲慢,心中不禁为之折服。他沉浸在甚深的法喜之中,早忘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了……[1]
同师子月的一席交谈使玄奘更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送走客僧后,他独自静坐了一会儿,便径去拜谒正法藏戒贤尊者。
见到玄奘,戒贤尊者自是非常高兴,玄奘这段日子讲经的盛况他是知道的,从这个出色的弟子身上,他看到了重振大乘瑜伽宗的希望。
“听说,东印度论师师子月专程来那烂陀寺找法师辩论?”尊者问道。
“那是小徒的误会。”玄奘恭敬答道,“师子月大师是来同弟子一起研讨佛法的。”
“哦?那么他现在在哪里?”
“他已经离开那烂陀,回菩提寺去了。”
戒贤尊者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这时侍者递上茶来,尊者轻轻接过,意欲同这位爱徒好好地聊上一聊。
那烂陀寺近年来内忧外患,大乘佛教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年迈的戒贤早已感觉到力不从心,玄奘的出现让他惊喜不已。那烂陀寺的僧众称颂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意思是“大乘之神”,在戒贤看来,这不仅是无上的荣耀,简直就是佛陀的旨意,要借这个青年求法僧来振兴大乘佛法。
他正思忖着如何开口,不想玄奘却先行起身顶礼,长跪合掌道:“弟子玄奘今日来此,是特来向师尊辞行的。”
“哦……”尊者放下茶,一时陷入了沉默。
对于玄奘的这个请求,他并不觉得意外。既然这位东土法师来印度的目的是求法,现在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选择回国弘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只是道路艰远,携经不易。除此之外,别的都构不成阻碍。
“法师现在回国,是不是太仓促了些?”迟疑片刻后,尊者终于开口问道。
“弟子暂时不回国。”
“可是法师刚才说要辞行……”
“是的。”玄奘道,“弟子是想以大乘瑜伽行者的身份,到五印各地游历观修,学习各部派经典。”
听了这话,尊者不禁皱起了眉头:“法师的佛学体系已经建立,登坛讲经时听者云集,百辩不倒,声誉日盛,已居寺中大德之列,何必贪多?”
玄奘微微摇头,垂目道:“玄奘学法未成就登坛讲经,是不合适的。”
他声音不大,却很坚决,戒贤尊者默默注视着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满心希望这位才华横溢又极具个性的关门弟子能够留下来,帮助自己重整那烂陀寺,光大护法菩萨的理论。但是现在看来,对方显然志不在此。
沉默良久,尊者终于长叹一声,道:“五印国土辽阔、地形复杂。东部多雨、南部酷热、西部又有沙漠。恐怕不适宜法师游学。”
玄奘没说什么。所谓国土辽阔、气候恶劣,都不是阻挡他脚步的理由。早在国内游学时他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行走经验,况且之后又经历了从大唐到印度这样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在他看来,大千世界,到处皆是路,没有什么不能走的地方。
戒贤毕竟是有道高僧,虽然心中万分不舍,却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攀缘的。沉默许久,终于沉声道:“既然如此,你去吧。”
玄奘心中感激,默默地向师尊顶礼拜别。尊者还想再说什么,终于忍住了没有开口。
菩提寺内,两名中年僧侣相对而坐。
“你也输给了那个边地来的僧人?”师子光睁大双眼,语气中透着吃惊。
“这很奇怪吗?”师子月目光平静地注视着师兄,“无论是学识还是定力,我在玄奘法师面前都望尘莫及,如果非要展开论战,我绝非他的对手。师兄又何必要我去自讨没趣?”
师子光质疑地看着他:“原来,你是不战而退,根本没有同他辩论,就认输了。”
师子月叹了口气:“师兄,难道我们不是修行人吗?为何你的心中只有‘输赢’二字?”
师子光蓦地起身:“难道那玄奘心中没有?”
师子月摇了摇头:“师兄,你的法执太重了。玄奘法师要我转告你,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太过年轻气盛,如果有什么冒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
师子光呆立片刻,缓慢地坐了下来:“他真这么说?”
师子月认真点头:“他还说,他一直都很敬重你,希望你能够重回那烂陀寺。另外,他认为自己的《会宗论》也有很多不妥之处。”
见师兄对此沉默不语,师子月不禁轻轻叹了口气:“师兄啊,你在那烂陀寺任教多年,一向受人敬重,却怎么仍存嫉妒之心呢?”
师子光哼了一声:“我并非嫉妒他,只是觉得他太过自以为是,而且在众人面前羞辱于我。”
“难道不是师兄首先自取其辱,然后这种屈辱才越来越多的吗?”师子月目不转睛地看着师兄,“你觉得他的骄傲让你难以忍受,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损于你自己的骄傲吗?你的烦恼究竟是因为你败给了他,还是因为失败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你鼓动我去同玄奘法师辩论,真的认为这样就可以洗刷掉你的耻辱了吗?师兄啊,你有这种想法,便违背了修行人的原则,不仅不能洗刷耻辱,只会令自己心中的污痕更多。”
师子光闭上眼睛,喟然长叹。
其实这些日子,他独自在菩提寺内也想了许多。摆脱了激烈的争辩,心情反而能够平静下来,对事情的始末进行反思,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般地步。他一直恼恨玄奘和戒贤,但也不能不承认,是自己火暴的性格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的。
师子月还想继续点化他:“你输给玄奘法师,这绝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相信有朝一日,你会为曾经同他辩论过一场而感到骄傲。”
“不必说了。”师子光摆了摆手,“我回那烂陀寺去见他。”
为避免尴尬,他们先去拜访海慧法师,向他说明来意,海慧叹道:“你们来晚了一步,玄奘法师昨日就已经离开那烂陀寺了。”
师子光不禁呆住:“离开?他为什么离开?他有没有说要去哪里?”
“这我也不太清楚。”海慧法师道,“听正法藏说,奘师觉得心中尚有疑问,而那烂陀寺无法为他解决这些疑问,他只得选择离开。”
师子月点了点头:“奘师也曾跟我说过,说要去五印各地游学,广诣名师。想不到这么快就成行了。”
说到这里,心中不禁掠过一丝萧索之意——我们如此有缘,为何就没有抓住这个缘法,同他一起走呢?
海慧法师叹道:“我们也觉得他走得太急了。可是他说,既然决定了要走,为什么不立刻动身呢?”
师子光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一个人走的?没带弟子和随侍吗?”
“没有。”海慧法师道,“听说他那两个弟子,室利般摩和摩离多罗一定要跟着走,被他劝住了。”
“为何?”
“奘师说,能够进入那烂陀寺学习,是千劫难逢的善缘,不可白白错过。他要弟子们珍惜这个机缘,留在寺中,好生修习。”
“哼!”师子光鄙夷地摇了摇头,“还说他不傲慢,要徒弟们在此修习,自己却选择离开,我看他压根儿就没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师子月皱了皱眉,尚未答话,就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缘,该走的必须走,该留的必须留。”
三人回头看时,却见接话的是天衣道人伐阇罗,他枯瘦的手中依然举着一根木棍,上面沾满蚂蚁,正吃得津津有味。
师子光的眉头皱了起来:“居士大概就属于应该走的。”
“错了。”伐阇罗笑得很开心,“我是最不该走的。虽说这那烂陀寺越来越没意思了,但我还是情愿留下来。”
海慧法师奇道:“为何你会觉得越来越没意思?”
“朋友接二连三地离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
师子月笑了:“奘师临走前有没有说过,他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伐阇罗的眼神有些落寞,“我问了他,他说居士既然会占卜,可以算一算。我说我不喜欢算这个。”
“是你根本算不到吧?”师子光嘲笑道。
伐阇罗瞥了他一眼:“师子光长老想是会算得很,奘师一走,你便回来了。不过我跟你说,奘师一定会回来的,到那时,你还得准备走。”
说罢,也不去管师子光恼怒的眼神,只管将手中吃净的树枝随手抛掉,扬长而去。
大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一月,玄奘离开那烂陀寺,身背竹箧,手牵白马,独自一人再度踏上了艰苦的游学之旅。
一切都和五年前初来时一样,这让许多人感到不解,在他们看来,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印度,不就是要到那烂陀寺学习《瑜伽师地论》吗?如今他求法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且获得了那烂陀寺上上下下的认可,成为寺中精通五十部经论的十大德之一,不留下来享受这份尊荣和名闻利养,却要离开这里,自讨苦吃,这也太奇怪了吧!
对此,玄奘没有做任何解释。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学法的成与不成,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跟别人如何解释得通呢?
佛陀在世时,弟子们来自不同的地区、种姓和民族,他们各自操持着完全不同的方言。在玄奘看来,中国的方言就已经很多很复杂了,而印度在这方面犹有甚之,其语言更多更杂。偏偏佛陀倡导众生平等,在他的教团中,各个种姓、各个民族的人都有,所使用的语言、方言更是五花八门。佛陀非但不要求他们统一语言,反而鼓励弟子们使用各种方言传播佛法。
据说,当年佛陀门下有一些出身婆罗门种姓的弟子,不止一次地提出要用梵文来统一语言,传播佛教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梵文是“雅语”,语言优美、规范,这对提升佛教的形象也有好处。
对此,佛陀的回答却是:“佛法不以美言为是,但使义不失,随诸众生,应以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
佛陀的做法无疑使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更加方便、灵活,也更接地气。但也为佛陀灭度后出现的各种分歧和矛盾埋下了隐患——在后来的时光里,僧团之中形成了很多区域性的派系,佛陀的学说也因此产生了差异。
早在进入那烂陀寺之前,玄奘就已经发现,印度半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典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随其方言有所差异。也就是说,自己要想学到更加全面准确的印度佛法,就必须把印度走上一遍。
玄奘一旦决定去做什么,就不会迟疑,更不会畏惧。何况即使是在那烂陀寺,他依然觉得自己所学太少,留下来已经没有多大进益。他希望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广泛游历,海纳百川。
玄奘首先踏上的是前往东印度的旅途。这条路较为平坦,视野开阔,沿途可看到北部遥远的雪山。恒河岸边的丛林里杂生着毕钵罗树、阿斯跋陀树、瞻博迦花树和各种灌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而在那些高大的树木附近,往往伴生着老山檀。一股自然沉稳、醇和悠长的香气透过黄棕色的树皮扑面而来,与香樟、香楠的那种刺鼻的浓香相比,略显清淡、温润,甚至还有几分淡淡的香甜气息。
玄奘不禁心生感慨,此木不愧是檀香中的极品,难怪五印度各宗派教徒都喜欢用它来做供具和法器。
除这些高大的树木外,绿荫中依稀还可见到一些淡红色的野葡萄和泛着白光的核桃果。在无风的日子里,它们看上去有气无力,一动不动地垂挂在树上,使空气中平添了一股热力……
在这森林密布、人迹罕至的地方,大象、犀牛、长颈鹿和野水牛随处可见,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直到进入伊孥钵伐多国,玄奘才算感觉到了一些人气。
这里是昔时慎那弗呾罗论师制《瑜伽师地释论》之所,也是贤爱论师、德光论师出家之处。有寺院十余所,天祠二十多所,婆罗门教的势力远大于佛教。
在其中一所寺院里,玄奘结识了两位高僧——恒他揭多毱多和羼底僧诃。两位大师擅讲《毗婆沙》《顺正理论》等经论,于是玄奘便暂留下来,跟随他们学习了半年之久。[2]
随后,玄奘沿恒河东行三百余里,抵达瞻波国,这里有十余所佛寺,僧二百余人,均习声闻乘佛教。[3]
同以往一样,玄奘走访各寺,与高僧们切磋讨论,虚心求教。由于没有了语言障碍,他所涉猎的内容更加广泛。
瞻波国的南部是一大片森林,绵延二百多里,娑罗树的红花怒放着。夜晚,皎洁的月亮从树梢间投射下银色的光辉,就在这空冥寂静的地方,修行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修道。
为防迷路,玄奘请了当地的一位向导带路。这向导面孔黝黑,十分健谈,边走边给玄奘讲故事——
“我们这里的国王是天女的后代,传说劫初之时,有天女下降人间,于恒河中戏水,因水灵触身,而生四子。现在的王城,便是其中一子的宫廷所在……”
类似这样的故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向导讲得兴致勃勃,玄奘也就姑且听之,偶尔听到感兴趣的,就记录下来。
就这样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大山之中,眼前出现了一座山洞,玄奘注意到,洞门前有块石头,坚硬光洁,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
“他原本是个牧牛人。”向导指着石头道,“每天都在这片山林中放牧他的数百头牛,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山洞。据说洞中景色很不寻常,花草遍地,犹如仙境。牧牛人看到一棵怪树,树间生满了黄赤如金的果实,他摘了一颗出来,却在洞口被恶魔拦截。牧牛人把果子塞进嘴里,恶魔竟扼住他的咽喉,他只好将果子咽了下去。”
“牧牛人吞了果子以后,身体开始变大,最后整个身体都陷在洞里出不去,只有头能伸出洞外。这样日复一日,牧牛人渐渐变成了石头。”
听完这个故事,玄奘的心中不禁有些恻然。他想,这个牧牛人似乎不能简单地说是贪婪,不过是多了几分好奇心而已,何至于受到这样的惩罚?
他忍不住看了看石头后面那个黑乎乎的洞口,不知怎的,竟想起了峨眉山上的九老洞。
“我想进去看看。”他突然说道。
“还是不要吧,法师。”向导紧张地阻拦道,“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敢进洞去的。”
一个无人敢进的山洞,自然会产生许多离奇古怪的传说。玄奘对此倒不在意,他出门在外,只要时间不是太紧,一向是见洞就钻的。在这方面,他的好奇心远甚于平常之人。
谢过向导后,玄奘独自牵马进了山洞。
洞内回环曲折,却也无甚稀奇。走了四五里地,眼前豁然开阔,却原来走到了另一个出口,这出口正对着的是一个幽静的山谷,谷内绿草如茵,周围是一大片高低错落摇曳不定的密林,娑罗树有数十丈高,上面挂满了红花。
玄奘忍不住想起《梨俱吠陀》里的一句诗——何谓森林?这即是将苍天与大地分劈开来的树木。
穿过娑罗树林,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不知名的树,这些树高数丈,灰黄色的树皮,枝条上长满锈红色的茸毛,厚厚的叶片一簇簇地聚集在树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极为鲜亮,数丈长的褐色藤蔓密密麻麻地纠缠在树干上。
这就是向导所说的那种奇怪的树吗?玄奘好奇地走在一棵树下,抬头朝上望去,果然看到一种奇特的果实从一大片叶子中透了出来,那果实有鸭蛋大小,深褐色,看上去竟同人的心脏一模一样!
玄奘蓦然想起,在瞻波国都城的一所寺院里,他曾见过一位来自达罗毗荼国的黑脸僧侣,那人跟他说起过这种能结出心形果实的植物,他们称之为“人心树”,称这种果子为“人心果”。据说,这种果子的汁液可使人心境宁静,有疾病的人吃了会很快痊愈,生命垂危者也会恢复健康。
“可惜,这种树现在已经不容易见到了。”记得当时,那僧侣遗憾地对他说道。
“为什么?”玄奘问道。
“因为这果子具有鉴人心、识善恶的作用,遇到恶人,或者言行不一的人就会突然变得枯干。”那僧人讲得活灵活现,“有人说它是属于来生的植物,还有人说它是阎浮提树的孩子。一些人对此深感恐惧,常在夜里偷偷将树砍倒。小时候,我所在的寺院里也有一棵人心树,粗大的树干上还有被斧头砍过的痕迹,据说是在我祖师时期被砍倒的。我的祖师是一位高僧,拥有还生之术,是他从雪山上取来甘泉,使树木又复活了,所结之果一颗也不少。”[4]
“现在这棵树还在吗?”玄奘问。
“不在了。”那僧人道,“我离开之前,有人放火将它烧掉了。”
这样的一种树,竟然无法在这世间生存,玄奘遗憾之际,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人心是多么脆弱,世人不顾一切地要摧毁人心树,恰恰说明了深藏心中的恐惧有多么深重。
玄奘没有想到,自己竟在这个不知名的山谷里见到了这种神奇的树,而且还是成片生长的,看来这里以前确实没有人来。那些只有一两寸见方的心形果实,真的具有鉴人心、识善恶的作用吗?
玄奘心中的好奇再也难以遏制,他抓住垂落在身边的一根藤蔓,三下两下便爬上了树,顺手摘下一颗果实,托在手上细看,那心形的果实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里,并没有丝毫变枯的迹象。
玄奘笑了——这是说明我的心得到了检验,还是说明,所谓的“人心果”仅仅是一个传说呢?
不管他了!他又摘下七八颗果实,兜在怀里下来,然后顺原路返回。
“那个牧牛人只摘了一颗果实就变成了石头,我比他还要过分,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玄奘兜着果子,边走边想,“如果有恶魔出现,我就跟他谈谈佛法,或许他会感兴趣的。”
他开始思考适合讲给恶魔听的佛法,不知不觉中,竟然很轻易地转出了洞口。
“看来,守洞的恶魔已经不在了。”站在人形石旁,玄奘一面想着,一面将没费多大事儿摘来的心形果实仔细包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神奇的果子带去东土,让它们在大唐的土地上扎下根来。
想来,喜欢猎奇的唐人应该不会惧怕这种果实吧?
离开瞻波国,玄奘继续向东,不久来到奔那伐弹那国。[5]
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经过迂回曲折的路途流经此地,在不远处与恒河汇合,在河口处形成了一片富饶的三角洲。
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向东,策马行走了两天,便到了羯罗拏苏伐剌那国,这里是玄奘印度之行的最东端,再往东去便是缅甸的国境了。[6]
早年在蜀地时,玄奘就听说过缅甸这个国家,成都东市里有许多口音古怪的商人,常贩卖些色泽鲜艳的织物。他们自称是从缅甸来的,还说,从他们的故乡到成都,只需要走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如此短暂的时间就可以回国了吗?就算是要先从印度进入缅甸的丛林,再向北而行,到达成都只怕也用不了半年吧?
难怪当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去西南一带开辟什么“蜀身毒道”,就是想通过西南地区,直接与“身毒”通商啊。
那是元狩元年的事情了,可惜张骞他们并没有到达身毒,使团在西南地区受到了一个名叫“夜郎”的小国的阻拦,还因此传出了“夜郎自大”的故事。
但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一条捷径。
玄奘被这突然冒出的想法吸引住了,心中竟涌出了几分久违的激动。
离开故国已历十载,一路奔波劳碌,他从未忘记自己求法的初衷。只是由于路途遥远,大量经像携带不易,每每思及于此,心头便不免闪过一丝忧虑,却不知佛陀于冥冥之中早已为他准备好了一条捷径……
刚想到这里,脚下的大地突然震动起来。玄奘惊讶回头,却见一大群瞪羚朝他飞奔过来,顺着河滩直向远方奔去,留下的沙尘和震动大地的蹄声,令人陡然生出几分铁骑交戈的恍惚之感。
“多像西域的野马群啊!”他的脑中不禁涌出一阵感慨。
想到西域,玄奘就觉得自己的一颗心猛地一动,那个似乎已经离他很遥远的绿洲国家又在他的心头浮现出来——在那里,他获得了西行以来的最大资助,并且拥有了一位异姓兄长。
我答应过兄长,取经回来去高昌,说法三年。无论如何也不能爽约。
离开高哈蒂后,玄奘再度折向西南,沿途巡礼圣迹。经三摩呾吒国,行五百多里,抵达恒河三角洲中部的耽摩栗底国。[7]
这个国家西南临胡格里河,有寺院十余所,僧侣一千多人,大多研修部派佛法。都城内还有几处圣迹,数十座婆罗门天祠,教徒众多。
玄奘并未去寺院挂单,而是径直来到都城东面的一座精舍。这里有一座阿育王时期的塔,建在高坡之上,为全城最高处,也是离海最近的建筑。
沿着石阶登上塔顶,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海涛声,玄奘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大海,看到那排山巨浪,接连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激起千朵浪花。
“大海的彼端就是僧伽罗国。”精舍守护人站在玄奘身边,长长的手臂朝东南方向一指,“当年阿育王曾依那个国家的王女僧伽蜜多之请,从大菩提树上取下一枝赠送给僧伽罗国,船便是从这里出海的。”
“可知这里是印度东渡的重要港口。”玄奘自语道。
守护人口中的僧伽罗国就是狮子国,一个诞生了提婆菩萨的地方,一个佛法兴盛的岛国,它的形状就像印度滴下的一滴眼泪。[8]
这个神秘的岛国与汉地的关系极为密切——后秦弘始十三年,法显大师曾到过那里,并从那里乘船归国;十几年后,狮子国的摩诃那摩国王派遣一个使团渡海来到中原,赠送了一尊玉佛和一枚佛牙的复制品。当时的中原佛教界希望建立比丘尼戒,国王得知后,又派了两个比丘尼僧团过去,帮助中原建立了比丘尼戒。
“我如何才能去僧伽罗国呢?”玄奘问。
“当然是登船涉海。”守护人道,“经过夜叉守护的海域,穿越飓风恶浪,行七百由旬,方可抵达彼岸。听说那里的宝石和珍珠非常著名,还生产最优质最名贵的香料。”
玄奘点头致谢,耽摩栗底国为东印度最大的贸易港口,要寻找渡海的船只应该不难。
注释:
[1]《会宗论》在那烂陀寺流行之后,一时间曾平息了中观、瑜伽之争,但并非说两派从此就再没有争论了。据中唐取经僧义净所传,玄奘离开了那烂陀近三十年,他的那番议论的影响依然存在,大家仍认为两派立说各据一意不必互相是非。所以义净在所撰《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中说:瑜伽则真有俗无,以三性为本;中观则中无俗有,实二谛为先。……既识分纲,理无和杂,各准圣智,诚难乖竞。
另一方面,中观学者还有从此立说更趋极端的,连清辨的议论都以为不彻底,这也可说是经过玄奘一度调和之后所激起的反应。
[2]伊孥钵伐多国,其位置大约是在今天印度的旁遮普省,距蒙哥马利约二十五公里的拉维河旧河床所在的哈拉巴;慎那弗呾罗,汉译“最胜子”。
[3]瞻波国,意译“无胜”,位于中印度吠舍离国南部,据英国考古学者康林汉姆考证,其位置在今天孟加拉的巴加铺。
[4]阎浮提树,印度神话中的一棵立于世界中心的通天达地的宇宙树和生命树,《摩诃婆罗多》里说,阎浮提树生长于须弥山南侧,其树之顶达于天,其果实硕大无比,跌落至地发出轰然巨响,然后射出银色果汁,形成围绕须弥山的河流。据说喝了这种果汁会永远止渴,并且青春常驻,能活到一万一千岁。
[5]奔那伐弹那国,位于今天孟加拉国的帕布那。
[6]羯罗拏苏伐剌那国,位于今天印度阿萨姆邦的高哈蒂一带。
[7]三摩呾吒国,在今天的恒河河口以西,直至呼格里河一带之地;耽摩栗底国,大约位于今天荷格里河右岸的坦鲁克。近年来发掘出不少遗物。
[8]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这里被视为是保存了最纯净佛教经典的地方,以佛法之岛而闻名。斯里兰卡也因此成为众多求法旅行者,尤其是那些希望了解佛祖最原始的佛经的人心目中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