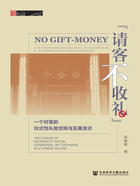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田野概况
一 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
为了研究礼物交换的变迁过程,我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调研。
第一个阶段是试探性调研,我于2014年6月18日至10月4日,主要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文献搜集、电话交流等方法在西县范围内开展调查。共参与观察了8次宴席,包括1次寿宴、1次周情宴、3次娶妻宴、2次嫁女宴、1次新生儿洗澡宴。对5名公务员、4名事业单位人员、1名国有企业员工、1名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文献搜集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政策文件,主要来源于村委会与县政府,特别关注发展规划、经济发展及与作风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另一部分是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资料,关注县域经济状况。这次调研的目的在于澄清请客收礼及不收礼的事实。此次调研发现,请客不收礼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不收礼的范围是不确定的、浮动的、有选择的,由此得出结论:收礼圈在缩小。
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12月4日至2015年3月21日、2015年4月11日至9月10日、2015年10月25日至12月2日,我在西村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选择田野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为何“不收礼”现象会出现,收礼圈为何会缩小;收礼圈缩小后,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基于这一目的,我将西村选择为田野点。为何选择西村?原因有三。第一是选择一个既有集市,但又不是完全市场化,而是传统文化有一定保留的村落,有利于分析市场及传统文化对于民俗的影响。西村既有自己的集市,又非镇行政中心,还是西县典型的宗族村落,各种祠堂建筑保留较好,民间信仰、宗族亦得到了复兴。第二是西县的村落分为上水片与下水片。我的家乡位于上水片,为了能选择一个有异文化感的村庄,我选择了下水片的村庄。西村就是下水片的村庄。第三,尽管西村有60%的人在外流动,但西村下辖四个行政村,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
通过朋友介绍和一位驻村干部的引荐,我进入西村做调研。2014年12月4日至2015年1月27日,我主要在西市访谈在那里生活的西村人;2015年2月2日至2015年3月21日,我入驻西村,参与观察并深入访谈小组组长,了解西村的基本情况,并参与观察西村春节期间至春分祭祖时期的宗族与民间信仰活动,了解村庄的文化生活;2015年4月11日至6月14日及2015年7月8日至9月10日,在西村进行田野调查,主要参与各类红白喜事,并与相关人物交流;2015年6月18日至7月6日,关注流动的西村人,对广州的西村人进行田野调查;2015年10月25日至12月2日继续在西村进行田野调查,主要关注几个关键报道人的日常生活与关系网络。其中,共被请去田野点参加4次丧礼、1次婚礼、1次乔迁宴、1次满月酒、1次小孩汤饼宴、1次10岁生日宴、1次60岁寿宴及1次升学宴。
第三个阶段是2017年8月2日至2017年8月15日,我重回西村,参与了1次婚礼。
基于上述调研,我共收集到19份礼单及请客名单,记录田野笔记27万余字。
由于我选择的是家乡的县城做研究,虽然做田野的村落并不是我家乡所在村,但是与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一样,都属于家乡研究。家乡研究有通语言的优势,但也有“文化约束”的问题。因为与田野对象共享一种文化规范,我反而需要遵从当地的一些习俗,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行。家乡研究其实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但我在突破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需要反思的方法问题,比如上祠的宗族活动禁忌女性、外姓参加,我最后也没能参加上祠的宗族活动。但是,我参加了下祠的宗族活动,如春分祭祖。理事长为了让我参加下祠的扫墓等祭祖活动,让我跟参与人员说自己也是同宗,也是邓姓成员。我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觉得这种方法仍然不太恰当。作为参与丧礼送旌[6]活动的唯一一位女性,我怀疑自己对村庄“男性送旌”的规范产生了影响。作为共享规则的本县人,我深知作为调查者的自己打破了许多应当遵循的本地文化规则,因此需要在此作一番交代。
另外,在田野中与田野对象聊天时,我会与田野对象聊“谁家最早开始不收礼”,人们的回答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回答说不知道,这种占多数;第二种回答是自己家,这种也占多数;第三种回答是自己认为的那家,这种回答较少。对于到底谁家率先“不收礼”,他们或者以为是自己家,或者认为不知道。为此,在调研中,我将发生宴请的时间进行了排序,基于人们对于“不收礼”的认知情况,将西村不收礼分为零散化(提供缺口)、打破(引领)、普遍化(两个连锁反应)三个阶段。
(二)个案研究:典型性及其代表性
本书属于单个案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它灵活,透过个案研究,能对事物了解得更深入、详细、全面,也更能把握事物的细节和复杂性(王宁,2007)。但是,个案研究面临典型性与代表性的问题。
第一,在典型性上,本书分析的是宴请不收礼的个案,这种宴请不收礼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收礼不同,具有特殊性。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赴宴送礼金、主人收礼金的随礼规则,礼金具有抵消开支的资助功能。因此,随礼中的资助型互惠与关系延续型互惠是一种普遍的互惠制度。然而,在本书研究的“不收礼”中,双重互惠制度发生了单重化与有限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典型性。以往的文献更多的是对“收礼”的研究,较少关注“不收礼”。因此,对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具有典型性。
第二,个案研究还涉及个案的代表性问题(王宁,2002,2007;卢晖临、李雪,2007;王富伟,2012;翟学伟,2014)。个案研究中的个案并不追求定量研究中对样本要求的“总体代表性”(样本能代表总体),而是追求结论的外推与扩大化(王宁,2002,2007),追求知识的增长(王富伟,2012),追求“类型代表性”(王宁,2007)。本书研究的个案亦是如此。
首先,从经验类型上来看,西村“请客不收礼”代表了“不收礼”的类型。西县及西村的“不收礼”不是唯一的现象。我对不同县的人进行访谈,了解到中国存在多种“请客不收礼”。一是普遍不收礼金,如广东广州和顺德、西省西县、湖南双凤乡和九龙乡、福建莆田和明溪城关乡等地都具有普遍不收礼金的现象;二是部分不收礼金,如浙江缙云斜陵村寿宴不收礼金,广东普宁沙溪房族间不收礼金、潮州惠来县迁居深圳的富人间不收礼金;三是个别不收礼金,如广东潮安富人回乡宴请时不收礼金,陕西西安岐山县及凤翔县收馒头不收礼金。由此可见,“不收礼”是礼物交换的一种类型。
其次,从经验意义上来看,研究请客不收礼的个案可以拓展对中国礼物交换的认识。费孝通很强调从个案研究中寻找中国经验。江村经济是他的一个研究起点,基于这个起点,他了解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在于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即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2001:236)。在这个基础上,费孝通(2006)对云南三村展开调查,寻找丰裕中国问题的新经验。与费孝通一样,本书旨在寻找并丰富中国的礼物交换经验。随礼是与中国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贺雪峰(2011)曾指出中国的随礼与人情交换在异化,本书所呈现的是随礼没有异化,而是在简化。我也可以同费孝通一样,在以后的研究中探索新的个案,同时与本书的个案进行比较,归纳理想类型。
再次,从理论视角上来说,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礼物与互惠变迁,可以丰富礼物与互惠研究的理论视野。在分析中国的礼物变迁时,贺雪峰(2011)从村庄共同体的性质的角度分析礼物交换规则的稳定化。他认为,南方宗族村庄可以通过公共规范约束人们的礼物交换行为,使得礼物交换不会异化,但他却假设南方团结村庄的公共规范是不变的。本书研究分析的也是南方宗族村庄,但是村庄的随礼规则却在发生变化。可见,不能继续从村庄结构的角度研究礼物交换。而本书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拓展礼物与互惠研究的理论视野。
最后,从理论意义上来说,研究“请客不收礼”能丰富互惠制度理论,产生新知识。国外关于互惠制度的研究没有区分出资助型互惠与关系延续型互惠,中国宴请随礼(金)的规矩使得中国存在与西方不同的双重互惠制度,这本身可以丰富互惠制度理论。本书的重点不仅在于分析双重互惠制度,还在于分析双重互惠制度的变化,即双重互惠的单重化与有限化,这就更能丰富互惠制度的研究。不仅如此,双重互惠制度的变迁具有外推效应。本书所分析的是资助型互惠消退,关系延续型互惠持续。广东顺德等地的普遍不收礼个案,也是资助型互惠的消退,关系延续型互惠的扩张。但是,与本书的个案变化发生于2000年以后不同,顺德的“不收礼”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生了。因此,在外推时还需要结合背景差异与新增变量。此外,双重互惠制度也可以用来讨论“收礼”且礼金标准逐渐升高的个案。这些地方其实是资助型互惠扩张,关系延续型互惠也在扩张。对于迁居城市的人而言,在城市中办仪式性宴请,可能会缩小宴请范围,相较于其原乡地,其收礼金的范围亦在缩小,资助型互惠及关系延续型互惠可能都在消退。对于这些地方,也可以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角度入手,分析双重互惠制度的变化。
二 田野概况
(一)西县概况
西县地处江西省东南部,东邻福建省,是江西进入闽西粤东必经之地。西县是一个典型的东南丘陵低山地区,地貌呈现“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与庄园”的特征。县域总面积1581.5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2111347亩,约占总面积的89%;耕地面积192646亩,约占总面积的10%;水面面积57794亩,约占总面积的3%;道路、城镇、村落、厂矿面积237230亩,约占总面积的10%。[7]西县在市域范围内是一个人口小县。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可知,县内常住人口为278246人,仅占所在市人口的3.32%,在市辖18个县市区中排名倒数第五;人口密度为175.82人/平方公里,排名倒数第八。县内常住人口中,男性为143821人,占总人口的51.69%;女性为134425人,占总人口的48.31%。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85692人,占总人口的30.8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192554人,占总人口69.20%。[8]目前,西县辖5镇5乡。
西县经济发展情况与全国省市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工业经济发展落后,整体经济发展层次较低。与全国省市经济发展相比较,第一,西县经济总量小。2012年,西县GDP为31.06亿元,占全国GDP的0.006%,比人口所占比重低0.018个百分点,仅达到人口所占比重的25%;占全省GDP的0.2%,比人口所占比重低0.5个百分点,仅达到人口所占比重的28.6%;占全市GDP的2.1%,比人口所占比重低1.3个百分点,仅达到人口所占比重的61.8%。与全国、全省、全市对比,西县经济总量明显偏小,尤其是占全国和全省的比重远低于人口占比。第二,西县第二产业比重相对较低。2012年,西县三次产业结构为33.6∶29.8∶36.6,第二产业比重分别比全国、全省、全市低15.5个、24个和16.4个百分点。第三,西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工业仍然以小微企业和个体作坊式工业为主。2012年,西县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2.1%,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4%、全省的48.9%、全市的55.3%;西县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1.8%,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0%、全省的66.9%、全市的77.2%。在全国省市都已进入半工业化阶段时,西县刚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9]2011年以来,县内致力于以三个工业园为龙头,重点发展环保设备制造、矿产品深加工、食品加工三大产业。其中摇床设备制造厂是主要的企业类型,但多以私人家庭作坊为主,因利润较高,企业主收入颇高。县内农业以白莲、烟叶种植为主,北部乡镇为重点种植区域。农民主要以种植白莲、烟叶创收。近年来,县城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与红色旅游,具体以县城南部区域为主。
西县外出工作人员较多,其职业类型有以下几种。一是生产线工人。西县大多数外出打工者集中于东莞、北京、温州、揭阳等地,主要在鞋业及纺织业企业中务工。特别是在东莞厚街镇,西县人具有规模效应,该区域内甚至有许多地道的西县特色餐馆。西县人在北京主要做调料生意。二是从事房地产行业。西县所在市内房地产开发商中,西县人所占比例较高。市内最早的房地产开发商便是西县人。此外,西县人还在温州、云南、湖南等地从事房地产行业。三是小企业主。西县人在东莞、广州、温州等地开设小企业,如东莞的鞋业加工企业、广州的纺织品加工企业及温州的小商品批发销售店。
西县多低山,交通向来不便。2010年以前,县内仅有2004年建成通车的G206国道。2010年G72高速横穿县内东西两轴及G35高速纵贯县城南北后,县内交通便利程度才有所提高。目前,县内仍未设置火车站。相较于市域其他县,西县交通相对封闭。
(二)西村概况
西村,位于西县南部,隶属西镇,地处该镇西部,距县城30公里,车程40分钟,206国道穿村而过。西村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乡,即西乡,新中国成立后撤乡,原西乡所在地被政府称为西村片区,包括四个行政村。西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村指该村村民仍然将西村的范围定格于原西乡的地理范围,其主要包括小西村、南村、北村、东村四个行政村(见图1-2),即西村片区。西村片区整体长大于宽,呈现椭圆形姿态,是典型的丘陵地形。至2012年年底,小西村辖14个村民小组,共486户、2160人,耕地面积1440亩;南村辖16个村民小组,共866户、3006人,耕地面积1525亩;北村辖13个村民小组,共537户、2560人,耕地面积1451亩;东村辖11个村民小组,共368户、1350人,耕地面积1168亩。西村外出人口较多,占总人数的60%。村内常住人口主要以白莲、烟叶、小米椒为重要的农民致富作物,每年每户平均种植的白莲在2亩左右,总种植面积在800亩以上,烟叶主要由神农氏种养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种植,每年种植面积在150亩左右。近几年发展的小米椒、芋头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成为该村的主要种植作物,目前该村已经形成白莲、烟叶传统作物种植和小米椒、芋头新兴作物种植四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格局。脐橙为赣南优势农产品,在该村也有少量种植。

图1-2 西村姓氏分布
村内习惯上将西村定义为自然村概念,由四个行政村组成。村内主要以邓姓为主,占80%之多,此外还有陈、邱、曾、黄、魏、张等姓氏。村内邓姓以祠堂为标志,划分为上祠与下祠(见图1-2)。上祠邓姓占80%,总祠为南阳堂(位于图中标号1处),供奉宗佑公;下祠邓姓占20%,总祠为明盛堂(位于图中标号A处)。虽然上下两祠成员在街道两旁有杂居,但总体上各房分呈聚居状态。南阳堂宗佑公生了三个儿子,称为长房(位于图中标号①处)、中房(位于图中标号②处)、尾房(位于图中标号③处)。长房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建有优公祠(位于图中标号①1处)、秀公祠(位于图中标号①2处)。长房优公后代人丁兴旺(其后代祠堂位于标有①1+处);中房人丁最少,男丁仅五百余人;尾房后代建有祠堂(位于图中标有③+处)。由图1-2可见,下祠明盛堂后代部分留于村内(其中一脉后代祠堂位于B处,B的后代祠堂位于C处),其他支脉大部分则迁居外地,其范围涉及隔壁村庄、隔壁县甚至隔壁省。西村的上祠、下祠被划分为四个行政村,以西村河及国道为界,河北面国道西面及国道东北处为东村,上祠长房后嗣大部分居住于此;河北面国道以东及河东南面部分为南村,上祠长房、中房、尾房后嗣均有居住;河北面南村以东为北村,上祠尾房后嗣主要居住于此;河南面近国道两旁则为小西村,上祠长房二子后嗣及下祠后嗣主要居住于此。平日习俗活动往往分祠进行。西村的赶集日子为逢农历的双日,即逢农历二四六八赶集,年关的赶集日子从正月初四开始。西村村民的信仰以道教与佛教为主,有显应庙、江东庙、张皇庙、观音堂、罗云禅寺等寺庙。其中,显应庙内供奉华光菩萨、案神及玉皇大帝;江东庙供奉项羽、虞姬及范增;张皇庙供奉张皇;观音堂为佛教寺庙;罗云禅寺为罗祖教宣传道场。西村的有神信仰者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许多西村的无神信仰者将老传统习俗以一种传承的姿态来运作,而非以信仰待之。西村的春节活动主要集中于西村显应庙及西村下祠,其中显应庙为上祠活动场所。西村逢双为圩,自清代便有圩市。西村圩市原位于老街,沿河不足百米,有单面店、合面店,且街面十分狭窄。1993年,政府组织在206国道旁边开发新街,是年秋开市。2004年新农村建设以来,西村中心的楼房建筑日益增多,街区面积不断扩大。西镇信用社、农业银行均在西村有分社。小西村、东村、南村及北村均设有村委会。
(三)田野对象的匿名化处理
最后,需要交代本书写作中涉及的田野对象匿名化处理事宜。基于学术伦理以及保护研究对象隐私的目的,本书中的市、镇、县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部分不重要的人物,采用姓氏加××的方式代替,或者直接以姓名首字母简写形式出现。我对相应的镇志、地方性政府资料,亦做了匿名化处理。书中使用的照片场是田野点的照片,以反映田野点的真实情况。但是,在田野点照片中,我基于保护田野点的原则,运用绘图软件对涉及田野点的相关祠堂名称、酒店名称、路名等做了匿名化处理,如图3-1中的“古天”“西江源”,图4-1中的“水深”二字,图5-1中右边的“公祠”二字,图6-1中的“邓”字,图6-2中的“南阳”二字,图7-1中的“西村邓”三字,都经过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