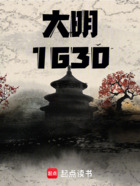
第5章 官逼民反
三月时节,陕北并不暖和,即便在县衙里,也有股寒意袭人。
“谢大人!”
卫渊拱了拱手,大马金刀的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这位叫丁猛的魁梧汉子给他上茶,道了声谢,便将茶盏置在案上静待下文。
丁弘誉绝不是酒囊饭袋。
寻常时候,外地官员到陕西任职并不稀奇,但在这样的乱世,对方来此,必是有所依仗。
汉子上完茶退到丁弘誉身旁,全程未发一言,只神色凛然地盯着卫渊,像是在防备。
“杭州府的龙井,清明前采的新茶,味道不错,卫少爷不妨尝尝,兴许会喜欢。”
“卫某一介粗人不会品茶,此番前来,只是想问问大人,捉拿家父所谓何事?”
“哦?”
见卫渊语气如此生硬,丁弘誉的声音也不由变冷了几分,嗤笑一声,才道:
“卫少爷竟然不知?”
“在下不知,在下只知卫家乃良善人家,家父几十年来更是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可你口中的良善人家,却非遵纪守法之民。十数年来,你卫家开私矿、贩私盐、豢养刀客、编练私军,收买人心,私铸甲胄劲弩,这些哪个不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我想你卫渊能分的清楚。”
说到这,丁弘誉突然站起身,双手撑着案台死死盯住眼前的少年郎:“你卫渊想干嘛?”
“在下只想保境安民罢了。”
卫渊好笑的看了他一眼。
怪不得都说,读书人的心最脏。
整个陕西,哪个大户家里没有私军刀客?现在以这个名目抓了卫世远,竟还能说的如此坦然。
“保境安民?”
丁弘誉像是听了个极冷的笑话,脸色愤然。
“县衙六门,衙役十人,皆是你卫家鹰犬;驿卒十骑,县兵百人,皆为你卫家爪牙。同官县百姓只知你卫家,不知有朝廷,这就是你说的保境安民?
你保的究竟是大明朝廷的境,还是你卫家的境?安的是朝廷的民,还是你卫家的民?
在本官看来,王嘉胤、高迎祥、王左挂他们这些巨贼又能算得什么呀?你卫渊才是同官县的大贼,卫家才是陕西省的巨寇!”
随着话音落去,气氛陡然变得僵硬。
卫渊颔首:“大人言重了。”
“说没说错,本官心中自有决断,卫少爷究竟要如何?”
“放了我爹。”
嘭——
丁弘誉气急拍案,震得案边茶盏悄然落地,发出道清脆的碎裂声响。
“你卫渊想干嘛?难道想进太庙嘛?”
说完这些话,丁弘誉仿佛瞬间被抽干了浑身的力气,跌坐在椅子上,盯着眼前面不改色的少年郎看了许久。
等再说话时,语气中已带着一丝乞求意味。
“听本官一句劝,把钱捐了,把粮纳了,把兵也散了。我去求杨大人,给你封个守备,镇守一方,保境安民。大明经不起你们这些强梁折腾了,只要你答应下来,我丁弘誉愿意一死,来偿还惊扰卫老爷的过失。”
“......”
看着跌坐椅子上的丁弘誉,卫渊眼睛里闪过一丝动容,但转瞬即逝。
“朝廷有大人,乃是朝廷之福,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大人熟读圣贤书,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此事容草民与长辈商议,草民告退!”
卫渊说完,转身离开大堂。
看着远去的少年郎,丁弘誉面如死灰。
丁猛在一旁悄声问道:“大人何不就此拿下这厮?”
丁弘誉嘴唇乌青,声音颤抖:“谁敢拿他......昨日金锁关来人,走前曾警告于我,若是县衙敢伤卫家少爷一根头发,消息散发之日,他们便玉石俱焚,届时大军攻城.......鸡犬不留不留呀。”
“王麟他怎敢?”
“朝廷已经镇不住天下这些强梁了。”
丁弘誉绝望地合上双眼。
......
卫渊刚走出县衙大门,卫山就迎了上来。
“大少爷,如何......”
“回去再说。”卫渊摇头,回头望了眼县衙。
二人向着城东的大宅走去,路上遇见向他问好之人,卫渊也会一一回应。
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他不知道再过几天,还能不能再回来。
回到大宅。
卫渊直奔书房,奋笔疾书。
不消片刻,他将五封书信写好,做好标记递给卫山。
“你去叫几个兄弟,将这几封信分别交给我舅、世奎叔父、杨师傅、继武,高大哥,让他们按照信上内容行事。吩咐兄弟们路上千万小心,万不可让信落入朝廷手中,必要时......”
“行,我懂!”
卫山接过书信,转身离开,顺手带上了房门。
过了一会,外面响起一阵马嘶声。
卫渊坐在紫檀木椅上,望着桌面怔怔出神。
他本想再过几年,等到朝廷在陕西彻底失势后再高举义旗,凭借自己这么多年的谋划,到时振臂一呼,九州幅裂不是难事。
为了这些安排,他这几年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地发展着家族势力,却因父亲这件事,彻底乱了方寸。
“早了,还是太早了。”
卫渊喃喃自语,拳头握紧又松开。
他这会心乱如麻,却不敢在外人面前显露半分,只有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彻底放松下来。
昏昏沉沉间,卫渊睡了过去。
他梦见了高楼大厦,梦见了飞机大炮,梦见了头顶的那面赤旗,梦见了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
......
同官县衙内。
卫渊离开后,丁弘誉招呼丁猛将他扶到了后宅中的书房,这次他只带了丁猛一人赴任,偌大的后宅中没有半点生气。
“猛子,坐,陪我说会子话。”
丁弘誉指了指旁边的椅子,一边研墨一边问道:“你跟我多久了?”
“记不清了,记得打记事起,就一直跟在少爷身边。”
“时间过的好快呀,我都四十一了,你也从那个小胖墩长成了壮小伙。”丁弘誉感慨一句,忽然笑了起来。
他从案前站起,提起毛笔,左手拉着袖角,闭上眼睛沉思许久才睁开。
簪花小楷跃然纸上。
“吾妻巧儿亲启
巧儿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卿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间一人;卿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
你我幼时相识,至今三十又一年矣。
犹记当年相识之时,卿之憨直,吾今思之,仍喜上心头。
二十吾加冠,次年与卿婚成。
吾骑高头大马,卿坐八抬大轿;三书六礼,三媒六聘;十里红妆,三年衣粮,你我喜结连理,修成结发夫妻......
......
......
丈夫许国,实乃幸事。
吾妻巧儿,莫哭!莫哭!
崇祯三年三月廿六日”
......